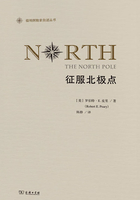
第3章 启程
1908年7月6日下午大约一点钟,罗斯福号从她在纽约东24大街尽头的休整码头的锚位向北起航,开始最后的探险。随着船退回到河里,来自数千名聚集在码头上向我们送别的人的欢呼声响彻布莱克威尔岛(Blackwell’s Island);与此同时,游艇船队、拖船和渡船号角齐鸣,致以良好的祝愿。一件有趣的巧合是,我们启程前往地球上最冷地点的那一天大概是纽约近几年最热的一天。那一天里,在大纽约有13人死于酷热并有72例中暑虚脱被记录,然而我们却要前往一个零下60°都不是例外的地区。
罗斯福号甲板上有大约100位皮里北极俱乐部的嘉宾跟我们一同启程,其中有几位俱乐部的成员,包括主席托马斯·H.哈伯德、副主席泽纳斯·克兰和秘书及司库赫伯特·L.布里奇曼。
随着我们顺河而下,喧闹声变得越来越大,发电站和工厂的汽笛声混入到内河船的嘟嘟声中向我们致意。在布莱克威尔岛,大量被收容者倾巢出动向我们挥手送别,他们的送别同样值得感激,因为是由为了社会的利益而被社会置于行动限制中的人送出的。不管怎样,他们祝我们顺利。我希望他们都享受现在的自由,并且要是能真的得到它就更好了。在托腾堡(Fort Totten)附近,我们经过了罗斯福总统的海上游艇五月花号(Mayflower),她的小信号枪发出离别致敬,同时官员和水手们都一边挥手一边欢呼。肯定从没有一艘船像罗斯福号那样被如此多的振奋人心的送别尾随着启程前往地球的尽头。
就在我们抵达步石灯塔(Stepping Stone Light)前,皮里夫人、皮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及嘉宾们和我自己都被转移到拖船纳基塔号(Narkeeta)上返回纽约。罗斯福号继续前往位于长岛牡蛎湾(Oyster Bay)的罗斯福总统避暑别墅,在那里,第二天皮里夫人和我将会跟罗斯福总统及夫人一起共进午餐。
西奥多·罗斯福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人,也是美国曾出现的最伟大的人。他拥有那种震慑人心的能量和热情,这是所有真实权力和成就的源泉。我们用他的名字给船命名,希望借助他的威名,努力开辟通向地球上最难以触及地点的路线,罗斯福号这个名字似乎是唯一和必然的选择。那作为理想在探险队前树立起力量、坚持、毅力和战胜障碍等特有品质,这些都已经使美国第26届总统如此伟大。
在酋长山(Sagamore Hill)那次最后的午宴过程中,罗斯福总统重申了他以前曾多次跟我说的话,那就是他对我的工作诚挚地和深刻地感兴趣,并且相信如果成功是有可能的话我将是成功的那一个。
午宴过后,罗斯福总统及夫人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子跟皮里夫人和我一起登上船。布里奇曼先生在甲板上,以皮里北极俱乐部的名义欢迎他们。罗斯福一家在船上停留了约一小时;总统视察了船的每个部分,跟包括船员在内的在场的每位探险队成员握手,甚至认识了我的爱斯基摩犬,北极星及其他几条狗,它们从我在缅因州海边的卡斯科湾(Casco Bay)的小岛上带了下来。当他跨过围栏时,我对他说:“总统先生,我将全力投入我所有的一切——体力的、脑力的和道义的。”而他回答,“我相信你,皮里,并且我相信你的成功——如果这在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
罗斯福号为等待捕鲸船而在新贝德福德港(New Bedford)停留,并且还在鹰岛(Eagle Island)做了一次短暂停留,那是我们在缅因州海滨的避暑地,我们把沉重的钢制备用舵搬上了船,为预防在将要到来的跟浮冰的激战中发生的故障而带上它。在前次探险中,当时我们没有额外的船舵,我们本也可以用两个。不过,这次事情的最终结果是,当我们有额外的船舵时,我并没有机会去用它。
我们离开鹰岛的时间是预定的,这样皮里夫人和我可以在船到的同一天乘火车抵达悉尼的布雷顿角(Cape Breton)。我对悉尼风景如画的小镇情有独钟。我曾八次从那里开始向北踏上北极的征程。我对小镇的记忆要回溯到1886年,当时我跟杰克曼船长一起乘着捕鲸船鹰号去到那里,在煤码头前停留了一两天,为我第一次的北方航行,格陵兰的夏日漫游,装满煤炭,在那次旅行期间,“北极狂热”控制住了我,从此再没有解脱。
从那时起,小镇已经从只有一家体面的旅馆和若干楼房的小定居点发展为繁荣市镇,有17000居民、许多工业和一家西半球最大的钢铁厂。我挑选悉尼作为出发点的理由是因为那里的煤矿。这是可以把船装满煤炭的地方中最接近北极地区的。
我的感情,在这最后一次离开悉尼当口,尽管难于描述,却与任何以前的探险开始时不同。当缆绳被解开时,我没有感到一丝不安,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做了每件可以确保成功的事情,并且每件必要的补给品都已经在船上。在以前的旅行中,我有时候曾感到焦虑,但是贯穿整个这次最后的探险,我没有让任何事情烦扰我。或许这样的自信感觉是因为每种可能的意外情况都已经被预防,或许因为过往所经历的挫折和致命打击已经麻木了我对危险的感觉。
罗斯福号在悉尼加煤后,我们穿过海湾到北悉尼装上最后几项补给品。当我们准备离开那里的码头,我们发现我们搁浅了,不得不停了一个小时左右等潮水涨起,其中一艘捕鲸船被挤在吊柱和码头侧边之间;不过在八次北极行动之后,一个人不会把这样的小事故当作是坏预兆。
7月17日下午大约3点半,我们在耀眼金色阳光下离开北悉尼。当我们通过信号站,他们向我们发信号,“再见,航行顺利”;我们应答,“感谢你们”,并且致了点旗礼。
一艘我们租用来送我们的客人们回到悉尼的小拖船一直尾随罗斯福号直到海港外的低点灯塔;在那儿拖船靠过来,皮里夫人及孩子们和波鲁普上校,还有其他两三位朋友上了拖船。当我五岁的儿子罗伯特向我吻别,他说,“快快回来,爸爸。”在不舍的目光里,我看着小拖船在蓝色的远方越来越小。又一次告别——已经有过太多次了!勇敢而高洁的妻子!你已经跟着我忍受了我所有北极工作的冲击。但是不知怎么地,这次离开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少了些忧伤。我认为我们都感觉这是最后一次了。
到星星出来的时候,在北悉尼运上船的最后几项补给品都已堆装,至少甲板对于一艘正在启程北航的北极船来说是空得有点不同寻常——除了后甲板之外,那里高高堆起了许多袋煤炭。
然而在船舱里,一切都是凌乱不堪。我的房间被塞满各种东西——乐器、书籍、家具、朋友们的礼物、补给品等——没有空间留给我。在我回来之后,有人问我在海上的第一天我是否在我的船舱里弹奏自动钢琴。我没有,绝妙的理由是我不能够靠近它。那些最初几个时辰的惊心动魄的经历主要跟在我的床铺区域挖掘出一个6英尺长2英尺宽的空间联系在一起,好让我在时间到来时在那里躺下睡觉。
我对我在罗斯福号上的小船舱有特殊的感情。它的尺寸和邻接浴室的舒适是我允许自己的仅有享受。船舱装饰简朴,由相配的黄松木搭建,涂上了白漆。它的方便性是北极地区长期经验的演进。它拥有一个内置的宽床铺、一个普通的写字台、几排书架、一把藤椅、一把办公椅和一个五斗橱,后面那几件家具是皮里夫人为我的舒适所贡献的。挂在自动钢琴上方是杰塞普先生的照片,而在侧壁上是一幅罗斯福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然后还有些旗帜,丝绸的是皮里夫人做的,我已经带着它很多年,还有我的大学联谊会德耳塔·卡帕·厄普西隆(Delta Kappa Epsilon)的会旗、海军联合会(Navy League)的会旗和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和平旗帜。那儿还有我在鹰岛上的家的照片和我女儿玛丽用那座岛上的松针做的香枕。
自动钢琴是来自我的朋友H. H.本尼迪克特(H. H. Benedict)的礼物,在我前次航行中成为我愉快的伙伴,而且这次它再度被证明是我最好的快乐来源之一。在我的收藏里至少有两百多首乐曲,不过《浮士德》的曲调在北冰洋上弹奏的比任何其他的都多。进行曲和歌曲也受到欢迎,还有圆舞曲《蓝色多瑙河》;而有时候,当我队伍的情绪相对处在低谷时,我们听我们特别喜爱的拉格泰姆乐曲。
在我的船舱里还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北极图书馆——就所有后来的航行而言绝对是完整的。这些书中间有各种小说和杂志,赖以消除北极漫漫长夜的单调乏味,我们发现针对这个目的它们是非常有用的。熬夜有时候意味着夜有一两月之长。
出发后第二天,木匠开始修复被挤坏的捕鲸船,用的是我们为此所带的木材。海浪汹涌,船甲板几乎整天都被冲刷。我的同伴们逐渐都在他们的船舱里安定下来;而如果某人犯了思乡病,可以背着他们独自待着。
我们的住舱位于舱面船室的后部,从主桅后面一点到后桅覆盖整个罗斯福号的船宽。中间是机舱,有天窗和锅炉的上风口,两边是船舱和餐室。我自己的舱室占据右舷尾角;向前是亨森的房间,右舷餐室和位于右舷前角的古塞尔医生的房间。左舷尾角是巴特莱特船长的房间,住着他本人和马文,向前依次是轮机长和他助手的舱室,膳务员珀西的舱室以及麦克米兰和波鲁普的舱室;然后大副和水手长在舱面船室左前角,接着是低级船员的左舷餐室。右舷伙食团的成员包括巴特莱特、古塞尔医生、马文、麦克米兰、波鲁普和我自己。
我将不会细述从悉尼到格陵兰约克角的第一阶段旅程,理由是那只是一次当季的舒适夏日巡航,任何正常大小的游艇都可以不冒风险地承担;而且有更多有趣和不寻常的事情可以写。穿过贝尔岛海峡,“船只墓地”,那儿总是有在雾中撞上冰山或者被强劲多变的洋流推上海岸的危险,正如任何会关心他的船的人一样,我整夜都没有睡。但是我禁不住把这次轻松的夏日旅程跟我们在1906年11月的回程对比,当时罗斯福号有一半时间是保持航向的,而剩余的时间是在随波逐流,失去了两个船舵,遭受海浪的猛击,在冰山季节沿拉布拉多海岸缓慢行进,穿越迷雾,并且在离岸仅有投石距离之时无意中发现爱情岬灯塔,只有爱情岬和秃头岬的警报声以及止步于海峡入口不敢尝试通过的大汽船的汽笛声为我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