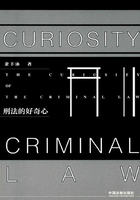
什么是盗窃罪Ⅱ
1
事物的轮廓止于边界,刑法也不例外。立法者在各个罪名之间夯入了界碑,相隔远的,这个分界线当然是清晰的,比如盗窃和杀人,贩毒和受贿之间。麻烦的地方在那些邻居们之间,远处看来,界碑也还是清晰的,有着明确的分界线,放大这根细线,看到的则会是一个模糊地带,如同海岸线到底有多长,取决于你用什么尺子来量。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常常围绕个案争吵,于是丈量总是要反复进行,新的碑石总是被腾挪又要安下,但模糊地带并不能被消除。盗窃罪的分界线内,是一个交糅着侵占、诈骗、勒索的模糊地带,各种观点经常争得死去活来。
先来看盗窃与侵占。直观的看法是,盗窃和侵占的区别是行为人事先是否合法地占有了财物,但实际上,法律观点的锅盖通常只能胡乱地盖住社会生活现实这口大锅,边沿上到处都是空隙。最简单的例子是,当甲向乙借钱时,乙借钱给了甲,之后甲却拿钱跑了,或拒不还款。你如何得知甲向乙借钱的意图是真是假,或者说产生侵吞钱款的念头是在借钱之前还是借钱之后?假若借款本身是个幌子,如何说借了款就是合法占有借款?同理,盗窃与诈骗的区分,也并不总是条理清晰。采用欺骗方式的盗窃和诈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害人交付财物时的心态,但被害人交付的产权是完整的,还仅仅是部分,也只有本人知晓。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对财产形态的利用更加多样化,财产可以被分割成不同的权益各行其是,很多时候,不再是财产的整体权利遭到破坏,而仅仅是财产中可被利用的某一部分。这些派生的罪名得以出现,相应地,也表明了刑法在扩展财产保护的界限。
如今,不再是一个依靠显露对秩序的违背而使盗窃行为获罪的时代,盗窃罪是在盗窃意图支配下不诚实获得财产的一种犯罪。而当司法机关试图对行为人的意图做出判断时,法律越细致反而让问题更复杂化了,在越不容易区分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指控陷入被动,而实质上,这些行为的可责难性、人身危险性和危害后果,并没有什么区别。与其把司法资源浪费于界定罪名边界的细微差异上,不如将它们统统打成一个包来处理。虽然在英美法系,亦曾在盗窃罪中发展出侵占和诈骗的新罪名,不过大体上我们能够看到一种联合的道路在慢慢呈现。英国《盗窃罪法》(1968年)和美国《模范刑法典》(1962年)的做法,是将盗窃、侵占、诈骗等行为都囊括在一个大的盗窃罪名里面,后者正被许多州采纳和实践。这也可以看作是实用主义在刑法领域的一个表现,至少是对情况相当复杂的盗窃罪如何追责的一种努力。
不过,将盗窃行为和诈骗行为放在同一个罪名之下,并不代表两者就没有区别,更明确地说,刑法上区分意义不大,不见得民法上也不大。美国法学家沃德·法恩斯沃在他的著作里曾考察过两个有意思的美国案例,两个案例中均有一幅丢失的油画,结局却不相同。第一个新泽西的案例中的油画是被盗走的,多次以全价转手后到了不知此画为赃物的甲手里,后来原主人发现了,要求甲归还。另一个纽约的案例中的油画是被骗走的,骗子携画逃跑,卖给了同样不知情的乙,后来原主人也发现了,要求乙归还。最终法律支持了新泽西的原主人,没有支持纽约的原主人。这两个案例的区别不就是在于油画是被偷走的还是被骗走的嘛,为何法律要来个区别对待呢?
不论是原主人,还是最后的买主,都应该谨慎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或弄清楚所购物品的来源,但是两者的难易程度的确有所不同。在诈骗案中,原主人跟骗子有面对面的接触,他更应该仔细辨识,更有机会来识破骗局;而在盗窃案中,被害人即原主人则无法做到这点,因此让买主去分辨油画的来源是否可疑更为有利些。也就是说,尽管都是财产遭受损失,但谁处于更有利的防范风险的地位是不同的。当然,防范成本最小的应该是窃贼和骗子,所以加给他们的责任也是最重的,即监禁和罚金。只不过通常他们也逃得最快,不一定抓得到人,那么,退而求其次,只好向原主人或最后的买家进行追讨了。但是这样的讨论还是很粗糙。难道新泽西的原主人不应该积极做好防盗措施吗?而纽约的买主也有审查油画来源的义务呀,最起码,如果油画的价格低得离谱还买下来,则法律会推定买主对于赃物具有明知,在这种情况下其主张又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的。沃德最后也指出了困难之处在于谁的防范成本最小,这在现实中并不好区分,具体到个案,也千差万别。新泽西的买主也有可能是善意的,并且支付了足够的价钱,他已经足够谨慎,实在无从发现这是幅盗赃,而另一个案子里,兴许原主人只要多一点点的谨慎就能防止盗窃案发生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支持原主人呢?
2
回到中国刑法,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区别。尽管作案的手段不同,也尽管《刑法修正案(八)》之后,盗窃也不再是纯粹以数额论处刑罚,但盗窃与诈骗、敲诈勒索这三个罪名,总体上是以侵犯的财产数额大小判处相应的刑罚的。以下是三者犯罪数额的比较:

从数额较大即构罪的标准来看,对盗窃罪的数额要求是最低的,诈骗和敲诈勒索都要高于前者。立法的这种区分是随意为之的,还是缜密思索的结果呢?再怎么说,立法都是一件很严谨的事,这样的区分必有其道理。对于诈骗来说,毕竟是由于被害人主动交付财物导致的,无论是关于中奖的短信诈骗,还是在大街上捡到假的金项链之类的行骗手段,都不可避免地有被害人的贪念在作怪,被害人的“配合”至关重要。尽管勒索者掌握的要挟不受法律支持,但通常这些或大或小的把柄却是被害人落下的。相比较而言,一般来说行窃者的行为与被害人并无交集,在盗窃罪里对被害人的责难是最小的。以诈骗罪来说,虽然法律条文上没有明确注明被害人也应负一定责任,但刑法却把犯罪数额的坐标向右移了一大段距离,盗窃罪的数额是1000~3000元,而诈骗罪的数额3000~1万元在其右侧紧挨着,考虑到诈骗罪的司法解释出台的时间要早两年,结合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两者的间距还会变大一些。
单从诈骗罪的追责来说,并没有看到对被害人的谴责,但与盗窃罪两相比较,则发现对被害人的责难,其实已经暗含于犯罪数额在追诉起点上的差异了。贷款诈骗罪(2万元,2010年)、合同诈骗罪(2万元,2010年)、票据诈骗罪(1万元,2010年)的追诉数额都要比单纯的诈骗罪高,这也显示了这类犯罪中,被害人与行骗者有更多更深入的接触,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分辨真伪,也因此要承担相应的风险。犯罪都是罪恶,不过某些犯罪也有一定的产出,诈骗之类的犯罪即是其中之一。当然,提高犯罪数额不单是责任分配,也有司法成本的问题,司法机关不可能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揽在手里,有限的资源更应该用在那些更严重的犯罪上。
法律对被害人谴责的难题在于界限如何把握,这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同犯罪中的过错认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也难以达成稳定的社会共识,具体到财产犯罪中,至少立法并没有在这一点上纠缠,仅仅点到为止,毕竟过错在犯罪分子这一边,几个罪名在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上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差异。因为,在一个精巧的骗局之下,一个很理性谨慎的人也可能会变得冲动盲从,不能要求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表现得从容睿智。历史上,始作俑者查尔斯·庞兹制造的庞氏骗局,被骗的数万人中,大多数是怀着快速发财梦的穷人。但麦道夫的骗局呢,其本质仍然是庞氏的套路,更贴近正常的投资回报率、麦道夫的身份标识以及维持20年之久的时间考验,使得骗局的伪装看起来更真,难以辨识。受害者也不再是普通人,名流、富翁、投资公司、基金会都不幸中招,即使是那些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和组织包括瑞士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国际奥委会等,它们的决策者们一样也无法生出一双火眼金睛来。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可那是事后,聪明的骗子们总能开拓出新的市场。
在骗局中,人们对于各式标签的抵抗力常常会变弱甚至丧失,这些标签可以是商标、品牌,也可以是身份、排场甚至一个名字就足够。在生活中,标签提供了一种快速便捷的方式让你做出决定,比如,你去看一部电影,总是首先关注谁是导演、谁是主演,越是大腕越吸引观众,而事实上在你没有看过电影之前,你并不知道电影好不好看,看过之后再大呼上当已经晚了,因为你已经为它花钱买了票。当然,你可以告诉朋友们这部电影不值得看,但对他们来说,在没有观影之前,对你的话也只能将信将疑,只有自己亲身观看之后才有定论,所以很可能他们仍将重蹈你的覆辙。况且,要是他是片子里某位主演的粉丝的话,你的话就更起不到作用了,标签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粉丝市场。现实情况往往是,口碑越差的影片反而有更加惊人的票房成绩。往更远的方向扯,有一个相当好的例子。2013年美剧《纸牌屋》的成功,首先得归功于制作公司Netflix的工程师们,而不是制片人和导演,他们在无数用户的点击、搜索、评分中找到了三个被很高关注的标签:BBC剧、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和老戏骨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然后让这三者都集合在这部电视剧里。事实上,他们赌对了,《纸牌屋》异常火爆,追看者超过了这个在线视频播放网站上的其他任何一部剧集。
3
弄清个罪之间的不同是深入了解一个罪名的好办法,但很显然,本文论述的方向并不是法教义学的,不是操作层面的技术分析,而是绕到背后,看到这些考量是否也有些道理所在。这样的论述很可能对司法办案起不了多大的直接用处,但或多或少的,在思维上可以注入一点新的东西。法律的多样、差异和变化,往往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的复杂性所致。
盗窃罪,好像是人人都知的一种犯罪,但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形变。很多年以来,本国教科书对盗窃罪的标准化定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暂且不论多次盗窃、入户盗窃这些被立法所囊括不久的行为,其实这些行为更可以印证前文中盗窃并非对财产权侵犯的那个观点。)这样的定义,不像严格限定的数学公式,只是一种归纳化的概括,所以大多数时候还够用,但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大多数行为人行窃的目的,是为了占有财物为其所用,概况而言包含了排除和利用两层意思,然而现实中剥夺他人所有,不见得就是永久性的,利用财物,更不见得依财物本来用途而使用。前者如张明楷教授举的例子,偷拿别人的司法考试复习材料,待考试结束后才归还,如此“借书”算不算偷?出了多年考题,他举的案例也绕不开司考!后者如一个有恋物癖的男性偷拿大量女性高档内衣,不是为了给自己穿,只是为了欣赏和意淫,这样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实践中,其实对这些行为定盗窃罪并无多少争议。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偷开机动车的司法解释(1997年)中规定“为练习开车、游乐等目的,多次偷开机动车辆,并且将机动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也是肯定了剥夺原主人对财物的所有即可构成盗窃罪。
另一个关于“秘密窃取”的讨论已经不计其数,“公开窃取”的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了。即使前者的理论中也发展出了“主观秘密”一说,也已捉襟见肘不够应付层出不穷的新状况了。比如,行为人明知室内有监控,亦明知有人看着监控,只不过料定人家即使发现了到赶来阻止时他早已经逃之夭夭了,如何评价这样的行为呢?又比如,行为人知道屋内有常年卧床不起但头脑清醒亦没有睡着的病人,任被害人眼巴巴地看着,只管在屋里搜东西,又如何评说秘密性何在?
盗窃罪的变形记不止上面说到的这些,几乎每一面的边界都在不断衍生、变化着。从侵犯的法益来看,盗窃罪走的是一条逐渐变窄的道路,最后宽度确定:这是侵犯财产权益的罪名。但《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后,盗窃罪又不仅仅是保护财产权,还涵盖了住宅安宁权、人身安全,路又被挖宽了。在另外的纬度上,盗窃罪却走得越来越宽广了。比如关于盗窃罪的对象,范围在扩大,差异在缩小。关于范围,能偷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不再局限于有形的物品,我们对于什么是有价值的认识,已经被时代的快速发展大大地向前扩展了,不只是无形的东西,比如偷电,盗打电话,窃取网络账号,斗地主赢来的欢乐豆,甚至包括了虚拟网络游戏中那些不菲的战斗装备,也不一定必须是合法的物品,在一个毒品交易频繁的社会,法律也必须对违禁品、赃物的窃取行为做出评价,在黑吃黑的情形中,法律的保护又从财产返回到了秩序。关于差异,只看被偷财物的价值几何,而不再看被偷财物的主人是谁,也许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古一今,在唐代,盗窃皇帝的祭祀、御用物品系“大不敬”,位列“十恶”,并非构成盗窃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也将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的死刑刑罚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