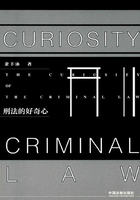
温故 罪名检视
什么是盗窃罪Ⅰ
1
人人都知道什么是盗窃罪,只有法学家是排除在外的。这还真不是一句打趣的话,因为大众朴素的观感,没有被严密拗口的法律概念所侵扰,对盗窃这类常见犯罪,压根不需要极力挖掘或探究,社会生活中千锤百炼出来的经验,就足够用了。糟糕的是,一旦变成法学家要面对的法律课题,反而变得没那么明显了。
起码有两个理由可以佐证。一是面对“许霆案”“梁丽案”这样一些案情十分清楚的案件,法学家们的意见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过。这跟舆论的强烈反响是两回事,后者主要是针对判决结果给出最直观的道德质疑,而法学家们溯本求源,对是否成立盗窃罪,是否成立犯罪竟然还争论得十分激烈,各执一词不愿认输。二是随处可见于法律报刊上对于某个新式侵财案件成立何罪的案例分析,盗窃总是和侵占、诈骗、抢夺甚至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侵权纠缠在一起。这些法律报刊主要是以法律实务工作者为阅读对象的,可见理论总是灰色的。
查阅列国现行刑法,盗窃罪总是被归于侵犯财产罪的类别之下,换句话说,盗窃罪被看成是侵犯了他人财产权的罪行。不管侵犯的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财产,所有权还是占有权,也不管采取暴力还是秘密手段,总之,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财产权益受到了损害。
然而,将盗窃罪归于侵犯财产罪之下,其实是一种很现代的观点。从英美法系的盗窃罪变迁情形来看,直到18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东第一次将盗窃罪归于对私人财产的侵犯,此后这个观点才逐渐被立法和司法沿用。
从历史上来看,盗窃罪的处罚目的并不着眼于保护财产不被侵吞,而是防止秩序被毁坏。盗窃罪在原初形态中之所以被视作犯罪,是由于其外显的偷盗行为,在早期社会里,很多法律中都有对现行犯的窃贼可以杀死的规定,比如《十二铜表法》中就规定了,对现行窃贼是可以动用私刑的,法律处罚的严苛,看起来是超出现代法律中罪行相适应的精神的,但这,怕也远不是 “野蛮”或“残酷”这样的词语就可以轻轻带过。事实上,早期盗窃所囊括的范围要广得多,法律并不区分贼盗、夜盗或强盗,这些行为的共性掩盖了他们之间的区别,他们都有一个类似的形象:侵入社区或者住宅,取走了不属于他们的财产,扰乱了人民的安宁感。这种外在的行为表现让人们感受到了犯罪的存在,也因此,那些“鬼鬼祟祟”“形迹可疑”才是形容盗窃犯罪恰当的词语。
这种现象是各个法系早期时的共同特征,如我们熟悉的那句政治格言:“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法经》虽然失遗,这句话却留了下来。这不仅是《法经》将《盗》立为六篇之首的缘故,也是此后中华法系各个朝代律法的通常做法。此处的“盗贼”不是今天所使用的语义中的“盗贼”。大体上来讲,“盗”不仅包括现代意义上的偷盗,也指涉强盗、抢劫;“贼”也不是小偷的同义词,指的是危害国家政权的人,乱臣贼子说的就是那些谋反的人们。将“盗”与“贼”同流合污成为一个固定搭配或词语,实际上说明了“盗”之危险不亚于“贼”。或者,以小观大,也可以把“盗”看成是较弱意义上的“贼”。国家的安全原本就植根于社区、村落、集镇,小块地方的安宁,才能聚集起大国的祥和。
这样看来,对于以往的起诉书或判决书中类似用“窜至”“逃窜”等词语描述的盗窃犯罪事实,似乎有了新解。不错,法律裁判力求客观、公正,正行进在脱离道德评判的道路上,也因此,这样的字眼总是要受到学者批判,认为这些词语是对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贬斥。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被“运动”的次数太多了,“扣帽子”都快成为某些人的本能了,法律文书也不免未洗脱掉全部来自专政化治理的色彩。也有另一种可能,或许这些词语的着重之处在于对犯罪的形象描述,正是这些向外展露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犯罪的发生。这未免不是代表了对诸如盗窃这类犯罪的古老又朴素的普遍看法的残迹,好比亿万年前宇宙大爆炸之后残留的微波背景辐射,那不是天线上的鸽子粪造成的。
奇怪的地方在于,罗马法中对于现行盗窃犯和事后人赃俱获者的处罚是不同的,对前者的处罚异常严酷,夜间抓获更可以不经审判当场处死。而对于后者,大多是以金钱赔偿方式了结。《出埃及记》中可以合法杀死的盗贼是掘地为盗者,这也属于现行犯。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展现盗窃罪的内核是那些惊扰安宁的行为,而非盗走财物的数额大小。在现代法律中,这两者不仅都囊括进了盗窃罪的范畴内,而且情况恰恰相反,前者中的大多数很可能只够得上未遂,依法还是从轻发落的正当理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分类体系,分属于法律的孩提时代和成熟时期。这是盗窃罪历史中一处陡然的转弯,法律有时候像一股乱流,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逆流的。
2
英美法系中对盗窃罪的第一个制定法定义,来自于1916年英国的盗窃法案(Larceny Act 1916),根据该法案,盗窃罪是指,未经所有者同意,欺骗并且没有善意的权利请求,以永久剥夺所有者权利的故意,获得并取走任何能够被盗走的物品的行为。这时候的立法也已经是很现代了,回溯那些更早时期的案例,对盗窃罪来说,普通法传统中尤其重视“侵入性地获取”这样一个重要特征,“没有侵入就没有盗窃”。这种“侵入”更多地传达了行为可被立即识别的观点,目击者看到之后,就会立即联想到犯罪的发生,真切感到社会秩序正受到威胁。
“侵入”在一种情况下会被否定:行为人在占有了原主的财产之后予以侵吞的行为,不构成盗窃,即“占有豁免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财物的占有和实际控制之间的裂缝已经越来越大,但在更早的时候,这两者的一致性非常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取走他人财物,并没有“侵入”发生,也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最典型的情况是,承运人将托运人的包裹予以出售或据为己有不构成盗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合法地占有了要承运的整个包裹。占有豁免原则的经典解释是,造成的损害属于私人,可以通过补偿方式弥补,法律不过多地入侵私人领域,尊重个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所以才予以豁免。
假若承运人将包裹打开,取走里面的物品呢?这种情况下,则一直存有争议,依据占有豁免原则,这仍然不构成盗窃。但1473年星座法院的一个案例突破了这个原则,从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打开缄封”规则。这个案件的事实一目了然:一个商人和承运人谈好价钱,要将几包染料送到南安普顿,承运人接收货物后,私自运到了另一个地方,打开封包取走了染料。承运人最终被判决犯有盗窃罪。取走的是整个包裹,还是里面的物品,竟然构成罪与非罪的分界线?看起来,法律在鼓励承运人不要打开包装,直接出售货物。从直觉上看,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另外一个矛盾在于仆人拿走主人家的物品,在普通法上则一直是构成盗窃罪。仆人在替主人管理家什时,为何又不享有占有豁免呢?
回答这样的问题,的确是让人捉襟见肘。犯罪是社会经验的凝结,立法的提炼并不与之时时合拍,法律尽管在不断变更,却并不是一以贯之,可以画出一条明朗的路线。不过,一个牵强而合理的解释大概还是因为这些行为看起来像是在犯罪。无论是承运人打开一个包裹,还是仆人拿走主人屋里的物品,都是以显于外部的形式昭示可疑之处。行文至此,仿佛所有的论述都是在重复前文所述的观点,甚至回到了开篇言及的普通人与法学家的对比,无论如何,骨子里的法律并不能超脱常人大众的观感太远,只成为法学家的领地。
但是,这样的观点亦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单从外部行为来判断犯罪与否,早已不是那么可靠,新的事物不断涌现,以往的法律不可能总有防备,比如,凭着真实或者假冒的信用卡到银行领取现金,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如何从这样类似平和的行为中做出判断呢?其二,除开经济财产领域,即使是暴力行为,有时候也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兴许那只是在电影拍摄的一个场景,而且往往比现实更加逼真。
3
著名的皮尔盗马案,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案情非常简单,一个叫皮尔的人从别人那里租了一匹马,但在他租马之后就将马卖掉了。皮尔占有马匹完全是基于被害人的交付,在已经获得占有权的情况下出售占有物,并没有任何侵入性行为。依从前文的分析,这符合占有豁免,亦不存在打开封缄的情形,按照先前的判例皮尔应该被判无罪。
皮尔最终被判犯有盗窃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盗窃罪实际上被扩展了。皮尔的整个行为之中你都看不到一个显露的盗马行为,让皮尔获罪的理由是他获取马匹时的意图,而不是一个看似犯罪的行为。这是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小案件,却将盗窃罪引上了另一条道路。
也许接下来的论述就该要为盗窃罪的转型寻找与之相互呼应的时代背景了。因为随后到来的19世纪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是贝卡利亚和边沁登上舞台的时代,是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被法律所重视的时代。惩罚不是目的,预防才是关键。惩罚是一种事后行为,是对于已经造成伤害后果行为的处罚,对于整个社会的利益却并不呈现帕累托增长,相反,惩罚要花费大量代价,成本高昂。只有事先的预防和震慑才能保护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利益,惩治盗窃要保护的是财产利益。
这样的分析固然不错,谁也无法否认时代精神的塑造作用,社会变革和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地会深入每一代人的心中,司法的变迁总有时代的印记,即使有意避之,也并不见得能躲开。不过,这样的解说仍不免太过于线条,过于教条,以后来者的辉煌为参照,赋予最先的某一个小事件以特殊的光芒,擅自建构最初本没有的意义,容易忽略整个历史纽带中的复杂多变和丰富细节。
对于皮尔盗马案的解释,其实还可以瞥见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起初这个判例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解。皮尔之所以被判有罪,并不是主审法官已经从盗窃意图里面看到法律应该积极追求预防功能,从而做出一个为后世所沿用的判例。
最初的解释仍然是,皮尔依靠欺骗获得了马匹的占有,在这样的意图支配下,可以推定其并没有占有马匹,也就是说这种占有是不合法的,不适用于占有豁免原则,之后皮尔又擅自将马匹卖掉,他的挪用行为就构成了对他人占有的侵夺,从而构成盗窃罪。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仍旧是陈旧的,只不过是将新的事实进行剪裁,使之符合原先的框架而已。
直到新的解释浮出水面,将盗窃意图置于那些偷盗的行为之前,我们才看到最初的判例被嵌进时代背景的墙缝。这是新的理论的重塑时刻,是回过头来,从一个案例中找寻到与后来的时代相符的内涵,而不是一开始就在一个判例中给予了契合了时代的解释。
对皮尔盗马案来说,什么时候卖马不再是重点,重点在于假意租马骗取马匹的时候,我们看到,法律观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转换,犯罪被认定是在前一个时刻成立。既然刑法的功用在于保护社会利益,警察和检察官的介入必须提前到来,危害发生之后再介入处罚的意义,远不及危害发生之前就受到制裁了。回过头来再看那个“打开封缄”原则,在先前的解释中原本还是一以贯之的,忽然地又变得可笑起来了,当承运人决定侵吞受委托运输的物品时,打开和不打开这个物品的包装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吗?于是,再对比前文中那个奇怪的罗马法规定和今日的法律变化,似乎也有了一个新解,法律的乱流之下亦有一条看不见的水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