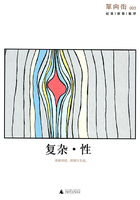
第8章 专题(8)
张曼玉的个性很直率,她觉得女性化就变得很做作。但我作为一个男性,反而可以去欣赏这些女性特质。有时候会带着自己的判断、批评,当我要处理电影里的女性角色,怎么转化,加上想象,加上我自己,会觉得,要是我是女人我会做得比你好看。
《单向街》:但是你所说的更“女人”这个部分,很有可能是本质化了“女性特质”,而且那有可能是小心眼、妒忌、还有柔弱,可能会遭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关锦鹏:男人也有,男人小心眼更可怕。所以我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电影导演,我只是一个拍女人戏的导演。
[三]
《单向街》:这些年,的确像你说的,很多香港导演都到内地来找项目,拍电影,两边的文化非常不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关锦鹏:刚才已经说过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香港电影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时间。整个氛围很宽松,拍电影的人很幸福,王晶可以拍通俗主流的电影,许鞍华可以拍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真正是百花齐放。但是我们不会排斥用大明星,因为香港电影工业基本上还是商业取向,那是包装,不过在包装的里面,我们有机会讲自己想讲的。
这几年在内地,不断有电影界的朋友告诉我,中国电影时代来了。每一年的数据显示,电影院的屏幕或者票房数字按多少百分比递增,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可能到香港电影当时的那种创作氛围。题材的选择上没那个自由。
可是香港电影也不可能回去了。大家都在缅怀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时候,很多人批评近几年香港电影已经没有了香港电影的特色,可是那个时代,有它特定的客观、主观环境。今天香港已经变了,哪怕我们死守在香港拍电影,也不见得能拍得出20世纪80年代那种电影。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们还没面对大陆的市场,今天哪怕你在香港拍戏,老板或者导演都有意识说,这个电影能到大陆去吗?到大陆去,肯定就有规限了。所以我个人反而用一个比较从容的态度去对待。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复兴香港电影,你就复兴得来。可能真的有机会,但不可能复兴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状态。
《单向街》:它可能有新的面貌。
关锦鹏:对,应该有新的面貌。另外你看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大投资有、小投资有、中型投资有,不一样的类型同期放映,各有各的观众,喜剧,鬼片,动作片,也可以是文艺片。但我觉得在内地这种氛围不见得会有,一下子几部都是武侠电影,《黄金甲》《十面埋伏》《无极》《夜宴》,观众很快会疲惫。香港电影为什么后来会衰退,就是它那种创意无尽的阶段过了。一部《英雄本色》出来,或者《笑傲江湖》出来,马上就会有十部这样子的电影,比较浮躁。我觉得中国电影将会很快跳到那个阶段,都是大制作,让观众疲惫。
《单向街》:是过度商业化的结果吗?
关锦鹏:说实在话,现在内地有哪一样东西不商业化?相比起来,文化创作出来的声音,或者让人看到的力度,跟大家已经富裕、很充足,手上的钱不知道往哪里花的经济状况,没办法相提并论。
《单向街》:那现在香港的大环境是什么样子?
关锦鹏:以前我到内地来拍戏,会抱怨说内地的工作团队跟不上我们的工作节奏,都比较慢。这一两年,不管上海还是北京,节奏快好多,反而回香港,觉得节奏慢了,有一种很舒坦的感觉。可是作为电影人,背后也有一点点感伤。尤其是享受过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本土拍电影的那种幸福,今天要来内地拍戏,要适应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会有一丝丝感伤。
《单向街》:在内地你最不能适应的是什么?是管制吗?
关锦鹏:我觉得管制还好,浮躁是让人很多时候很疲惫的。
《单向街》:这种浮躁是?
关锦鹏:体现在各个方面。你会很明显觉得已经有钱的人,很多时候在炫耀自己有钱,还没有钱的人哪怕不说,其实心有点急——为什么人家可以这么有钱,我还那么穷?有一些搞创作的人,比如说会要求说这个花一定要什么样,多贵我都要,假花我要不了。那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浮躁。我记得,张叔平有时候知道我不会拍花的特写,他就把两瓶假花放在后面,形状颜色很像真的,而且你那场戏拍三天,它就在那儿,更容易接戏。这是点点滴滴感觉到的。
《单向街》:你之前说明朝末年和现在很像,是指?
关锦鹏:就是在太平盛世,明朝的时候,连朝鲜、日本都是它的附属国。在一个大的制度底下,一票文人都辞官,回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诉之于他们的创作,以情说理。肯定意味着,这种繁华鼎盛的背后有很多被扭曲的东西。
《单向街》:被扭曲的东西指的是?
关锦鹏:可能在大的环境底下有很多敢怒不敢言,或者就把所有心思放在怎么赚钱上面。
同志仍需努力
文/迈克
幸亏自己生得晚,不必经历同性恋的苦难年代,开始恐惧真的过去了吗?
去年中通长途电话的时候,陆离说要送我一本小书,电脑鼻祖图灵[1](Alan Turing)的小传。她大概听出对科学向来没兴趣的受惠人不大热衷,于是卖了个小关子:“看了你就明白为什么。”以她缜密的心思,一定不是希望成功人物传记发挥鼓舞作用,令孺子临老入花丛,但再好奇也不敢劳烦她邮寄,反正秋季打算回港,请她到时再想个法子交递。
如是者拖了几个月,待得我奔走于尖沙咀铜锣湾,深居简出的她自然不可能为礼物抛头露面,本来想趁她丈夫星期天远足之便交给一位共同朋友,结果也不成事。眼看亚洲之旅将近尾声,接收图灵仍然遥遥无期,她终于忍不住透过电话揭露谜底:“书里写他15岁那年爱上密码,同时爱上同学Christopher!”我虽然有点头绪,就是作不出适当反应,支支吾吾发出“??”的空洞回音。她实在想不到有人会蠢钝若此,只好提高声线:“Christopher呀!男同学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蛮力,居然立刻答:“可是陆离,15岁爱上男同学比你想像中普遍得多哩,尤其在英国的寄宿学校。”什么叫狗咬吕洞宾,这是最佳示范。你以为谁都是自小奔驰于同志绿茵场的老马,撞口撞面无一不是龙阳君,坦荡荡身穿背心以示有断袖之癖?前辈的一番好意我怎可以那么鲁莽,不假思索以“何必大惊小怪”的语气顶撞?
两星期前书辗转传到手上,翻开来更教人羞惭交加:她唯恐收书人无心向学,亲手列了索引注明景点页数,由“15岁爱上密码和Christopher”至“1954年6月7日山埃苹果”,井井有条一清二楚。1921年出生的图灵,成长于同性恋仍属犯法的时代,浑浑噩噩的初恋,因对象夭折而划上句号,传记指“不能正视自己情感”的他终生有性无爱,最后还因为误交小混混而身败名裂,直到2008年9月才正式获得平反。
读着这种历史悲剧,我总暗暗捏一把冷汗,庆幸自己生得晚,身心都不必暗渡陈仓。蕉风椰雨的环境,出乎意料善待夹缝中的边缘人,因同性相吸而锒铛入狱的风化案虽然偶有所闻,对活在小圈子自给自足的少年完全不构成威胁——念中学时,我就有谈得来的同志同学,既勤奋修练嗜好与品味,也努力实习性和爱。20岁一头栽进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三藩市,简直菩萨保佑放虎归山,开正戏路也文也武。说出来你不会相信,那时我非常天真,以为美国人一向都那么开放,不晓得解开枷锁的石墙起义只是四五年前的事,而Harvey Milk[2]正处于现在进行式。
长期逸乐不知民间疾苦,尽管并非天天搂着昏君奸妃酒池肉林,毕竟脱离一般群众摸黑慰藉欲望的现实——当然瞒天过海偷香窃玉也是一种乐趣。近年接触的人品流比较混杂,多少学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事物,然而还是很难洗涤玛丽安东妮特情结——法国大革命革掉美人头的皇后,名句是“没面包吃为什么不吃糕饼?”譬如读到南洋政客一而再被控鸡奸的新闻,绘形绘声报导当事人肛门验出有被告之精液,我就禁不住尖叫:这位先生与陌生人发生肉体关系怎么不戴安全套?太没有卫生意识了!接下来又质疑:担任零号角色的,事后为什么没有即时进行清洁工作,忙着观看树木而忽略了森林。
又譬如,最近翻译电影《单身男人》(A Single Man)字幕,执导的Tom Ford[3]虽然是美艺潮流教主,但对白本几乎令人误会是古装片。男主角在加州大学教文学,课堂上借赫胥黎的《夏去夏来天鹅逝》为弱势社群伸张正义,说来说去,还是一派王尔德的遗风,“同性恋”卡在喉咙,不折不扣“不敢报上名字的爱”。声东击西的招式,媲美奥斯汀笔下的闺秀,又如张爱玲《花凋》那位留学维也纳的章云藩医生,措词也过分留神些,“好”是“好”,“坏”是“不怎么太好”,“恨”是“不怎么太喜欢”。既然有意为自己人抱不平,表明身份也是一种姿态呀,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何必远兜远转由纳粹主义说起?
回心一想,我这可不是强人所难么?剧本根据克里斯多夫·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64年的小说改编,当时二战结束尚不满二十年,美国社会依然吹着冷战寒风,断袖分桃和“XX党”一样是见光死的罪状,怎可能要求孩子王脱下保护性取向的盔甲,赤条条晒不存在的太阳?恃着拥有引以为傲的古铜色皮肤,讪笑别人无可奈何的苍白,犯的正是夏虫不可语冰的毛病。
不过,最教人伤感的是,译着译着,我渐渐发觉戏中人的担忧、顾忌、避讳和恐惧,其实并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即使天生缺乏被逼害焦虑,周围的气候也不算太坏,我很难欺骗自己“美丽新世界”[4]十全十美——赫胥黎名着的原题,那个形容词不是“美丽”而是“勇敢”,更适宜借来暂用。同志仍需努力啊,山埃(一级剧毒氰化物,俗称山埃,英文名称potassiumcyanide)苹果已经让图灵捷足先登抢去吃了,我们不稀罕当等待王子拯救的白雪公主,我们要当穿本季最威风时装的恶毒皇后!
注释:
[1]阿兰·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6.23—1954.6.7),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
[2]Harvey Bernard Milk,1930年5月22日~1978年11月27日,美国同性恋运动人士,也是美国政坛中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人,1978年,当选旧金山市政管理委员会第五区的委员。
[3]Tom Ford,1962年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全球顶级时尚设计师,曾担任Gucci、YSL等品牌的创作总监。
[4]《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亦名“勇敢面对新世界”。为英国作家阿道斯·雷欧那德·赫胥黎于1931年创作1932年发表的反乌托邦作品。与《一九八四》和《我们》并列为“世界三大反乌托邦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