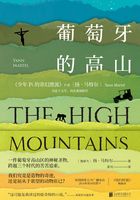
第9章 无家可归(9)
这样一种污秽的液体,店主和药剂师怎么就不问问他为何需要那么多?他当作燃料购买,他们却当作杀虫剂售卖。他们以为他是一场寄生虫聚成的龙卷风,他的头顶是欢快起舞的虱子、跳蚤及其同类的国度。难怪他们从不正眼瞧他。他愣住了。显然如此。显然如此。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解释。店主和药剂师猜得没错。他浑身奇痒,痒到几近癫狂,恰恰因为他就是一场寄生虫聚成的龙卷风,他的头顶就是欢快起舞的虱子、跳蚤及其同类的国度。
他看了看另一只手。他正在倾倒的那只瓶子已经见底了。
这是最后一瓶。他原本有多少?差不多十五瓶。旅途伊始,车厢里就装了好些汽油瓶,它们堆在油桶旁边,一路咣当作响。现在他一瓶也没了,多一瓶也找不到。他抠住油箱小小的圆形开口,好像可以将它拉开似的。他做不到。一只装满汽油的浴缸能让他从当下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但在痛苦与解脱之间还隔着一道窄门,它死死紧闭。
他想知道,是谁碰过他?是谁碰过他的衣服?是谁把寄生虫传染给他的?他一定是在波沃阿-德圣伊里亚或者蓬蒂-德索尔被传染的。在那两地他都蹭到了别人的肩膀。为了把汽车从围观的人群中拯救出来,他还是贴着人们的身体蹭过去的。
他把自己从上到下疯狂地挠了一遍。
天空变得阴沉。雨点落下来,他钻进车内避雨。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汇成变幻的条纹,模糊了他的视线。雨越下越大,直至暴雨倾盆,他这才想起伯父从没提过汽车在雨中的性能。他不敢冒雨驾驶,决定等到雨停。
黄昏与黑夜相继浮现,形如瘴气。睡梦中几辆马车从四面八方朝他飞驰而来。他浑身冰冷。他的脚从驾驶室的边缘伸出车外,被雨浇得透湿。浑身的瘙痒也不时让他醒来。
到了早晨,雨依旧下个不停。天太冷了,他可不想在雨里洗澡,只能打湿双手擦了把脸。唯一的宽慰来自乌利塞斯神父在岛上经受的苦雨。那里暴雨如注,日夜不息,简直让人精神错乱。相形之下,这场温和的欧陆细雨算得了什么?
这条荒凉的小道只有农夫偶尔经过,他们无一例外地停下脚步,和他聊上几句。有些人沿路走来,要么独行,要么牵着一头驴;其他人则穿过农田走来,他们是正在巡视自己小小领地的农场主。每个人似乎都对打在身上的雨点毫不在意。
农夫一个接一个,反应如出一辙。他们察看车轮,觉得它们精致小巧。他们端详后视镜,觉得它们妙不可言。他们打量控制台,觉得它令人生畏。他们凝视引擎,觉得它高深莫测。每个人都认为这辆汽车是个奇迹。
唯一例外的是一个牧羊人。他看起来对这个新鲜玩意儿并不感冒。“我能在你旁边坐一会儿吗?”他问,“我淋湿了,很冷。”
他的羊已经把汽车团团围住,外面有一条小个儿的牧羊犬围着羊群绕圈,一边汪汪直吠。羊群的咩咩声绵延不绝,让人坐立不安。托马斯向那人点了点头。他绕到车的另一侧,爬进驾驶室,在托马斯身旁坐下来。
托马斯期待他开口说话,但那个古板的老头两眼直视前方,一言不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沙沙的雨声连绵不断,羊在叫,狗在吠,沉默分外鲜明。
最后还是托马斯先开口。“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旅行。这段路非常艰苦。我在寻找一件失落的珍宝。我花了一年时间确定它可能的方位。现在我知道了,或者说我就快知道了。我已经很接近了。一旦找到,我会把它带回里斯本的国家古代艺术博物馆,其实它配得上巴黎或者伦敦的一流博物馆。我说的这件东西,它——嗯,我不能告诉你它是什么,但它是一件惊世之物。它会让人瞠目结舌。它会让观者哗然。有了这件东西,上帝会为他对我挚爱之人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乡下老头唯一的反应不过是看了他一眼,然后点点头。除此之外,似乎只有羊群听懂了他心血来潮的自白,齐声发出一波“唉——”的叹息。这群羊可不是童话里乳白色的蓬松云朵。这些家伙长着瘦骨嶙峋的脸、凸起的眼球,身上的羊毛坑坑洼洼,屁股上沾满了粪便。
“跟我说说,”他问牧羊人,“你对动物怎么看?”
那个牧羊人又看了他一眼,不过这次他开口了。“什么动物?”
“嗯,比如这些动物,”托马斯回答,“你怎么看你的羊?”
那人一字一顿地说:“我靠它们过日子。”
托马斯沉吟了片刻。“是的,靠它们过日子。你的话很深刻。要是没有你的羊,你就过不了日子,你就得死。这种依赖性创造了某种平等,对吗?不限于你个人,而是对整体而言。在你和羊的组合里,你们位于跷跷板的两端,中间某处有个支点。你必须保持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比它们更强。”
那人对他的话无动于衷。这时托马斯身上忽然一阵奇痒。
现在瘙痒已经遍布全身。“对不起,我有些事情要处理。”他对牧羊人说。他沿着车侧的踏板移进车厢。在车厢里,透过宽敞的前窗,牧羊人的后脑勺清晰可见。托马斯在沙发上辗转翻滚,用指甲冲着折磨他的小恶魔们一阵乱挠,以压制瘙痒。强烈的满足感随之而来。牧羊人没有回头看一眼。
为了遮风避雨,他挂起一张毯子挡住破碎的侧窗,并用车门把它夹紧。雨水敲落在车顶,化作单调的鼓点。他拨开零乱的装备,在皮沙发上为自己辟出一块容身之所,然后用另一条毯子把自己裹好,紧紧蜷起身子……
他蓦地惊醒。他不知自己睡了五分钟还是五十五分钟。雨依然在下,牧羊人已不见了踪影。他透过雨痕密布的车窗望出去,看见前方路上一团隐约的灰影——那群绵羊。他打开车门,站上踏板。牧羊人在羊群中间,仿佛行走在云端。狗仍旧绕着羊群奔跑,不过托马斯已经听不见它的叫声。羊群沿路远去,从路旁拥入一条去往乡间的岔道。
托马斯透过雨帘看着羊群渐渐变小。就在它们即将消失在一道山脊背后时,那个已经缩小成一个黑点的牧羊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他是在寻找某只走散的羊,还是在看他?托马斯使劲挥手。他也不知道那人是否注意到他的告别。黑点消失了。
他回到驾驶室。副驾驶座上放着一只小包裹。拆开包裹,里面有一块面包、一块白色乳酪和一小罐封好的蜂蜜。这是圣诞礼物吗?圣诞节是哪天?还有四天吗?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记不清日期。无论如何,这是牧羊人的馈赠。他深受感动。于是他大快朵颐。太美味了!他不记得何时曾享用过如此可口的面包,如此美味的奶酪,如此香甜的蜂蜜。
雨停了,天空渐渐转晴。在等待冬日的阳光烘干路面的工夫,他给车上了机油。然后他迫不及待地上路了。路过小镇阿雷什时,他步行进了城。运气不错,他找到一间像样的药店。
“你的存货我全要了。我那几匹马身上全是虱子。”柜台后的男人拿出常见的小瓶汽油时,托马斯对他说。
“你可以去问问伊波利托,那个铁匠。”药剂师说。
“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我猜是马给他带来了生意,包括那些身上爬满虱子的马。你的脚怎么了?”
“我的脚?”
“是的。出什么问题了?”
“我的脚没问题。为什么这么问?”
“我看见你是怎么走路的。”
“我的脚非常健康。”
托马斯迈着那双非常健康的脚,倒着穿过小镇,在一条小巷里找到伊波利托的铁匠铺。他惊喜地发现这位铁匠居然有一只巨大的汽油桶。托马斯高兴得简直要晕过去了。这些库存不仅足够喂饱他的汽车,还能抚慰他饱受蹂躏的身体。
“兄弟,我需要很多。我有十二匹马,它们身上全是虱子。”
“哦,你不能把这玩意儿用在马身上,会伤到它们的。它对皮肤的腐蚀很厉害。你需要一种兑水的粉末。”
“那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汽油?拿来干什么?”
“给汽车用的。那是一种新式机器。”
“太棒了!我就有一辆,而且正好需要加油了。”
“你刚才怎么不说?”那个乡下人乐呵呵地说。
“我一心惦记着我的马。那些可怜的牲口。”
托马斯对那十二匹受苦的马的真挚关爱令铁匠伊波利托大为感动。他耐心细致地讲解:如何用热水冲兑去虱粉,仅须涂抹患处,晾干之后再小心梳理、清除虱子。从头部开始,往后往下梳遍全身。这是个很费时的活儿,但爱马之人理当如此。
“把你的马牵来,我帮你处理。”伊波利托出于相同的爱马之心,不由得脱口而出。
“我不住在附近。我是开车来的。”
“看来你为了这种错误的药跑了很长一段路。我就有这种粉末。你刚才说十二匹马?六筒应该够了,八筒保险一点儿。你还需要梳洗的工具,保证品质上佳。”
“谢谢。我真是松了口气。你卖汽油多久了?”
“差不多六个月。”
“生意好吗?”
“你是我的第一个顾客!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汽车呢。不过别人跟我说,它是马车的未来。我可是个精明的生意人,说真的。我懂得经商之道。与时俱进非常重要。没人想买过时的东西。你需要成为第一个传播消息、展示商品的人。这是垄断市场的诀窍。”
“你是怎么把这一大桶汽油搬来的?”
“用马车运来的。”
听到这个词,托马斯心里一颤。
“不过你懂的,”伊波利托补充道,“我没告诉他们这是给汽车用的。我说是用来给马匹除虱的。他们对汽车的态度很奇怪,那帮赶车的。”
“是吗?快有马车来了吗?”
“哦,大概再过一个小时。”
托马斯撒腿朝他的车跑去,他是面朝前跑的。
他挟着银行劫匪的气势,在轰鸣声中开着伯父的雷诺回到铁匠铺。面对托马斯带来的这台躁动吵闹的机器,伊波利托又惊又喜,同时难掩惧色。
“这就是汽车?真是个吵死人的大家伙!我得说,这是一种美丽的丑陋。让我想起了我老婆。”伊波利托大声说。
托马斯熄了火。“我完全同意——我指的是汽车的部分。老实说,我觉得它是一种丑陋的丑陋。”
“嗯,也许你是对的。”铁匠陷入了沉思,大概在思考汽车将怎样毁掉他的生意和生活方式。他皱起了眉头。“好吧,生意归生意。汽油从哪儿灌进去?指给我看看。”
托马斯急切地伸出手指。“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他让伊波利托灌满了油箱、油桶和所有装除虫剂的玻璃瓶。他焦急地盯着那些瓶子,迫不及待想举起一瓶把自己全身浇透。
托马斯付了油钱,又要了八筒马用去虱粉和品质上佳的梳洗套装。“欢迎下次再来!”伊波利托高声喊道,“记住,逆着毛从后往前梳。从头开始,往后往下梳遍全身。可怜的牲口!”
“谢谢,谢谢!”托马斯一边加速离开一边高喊道。
出了阿雷什,他离开大路,拐上一条有路标的岔道,希望绕过人口密集的尼萨城。他相信,即使地图上小路的标志模糊不清,它也能指引他绕过尼萨,重返大路。拐进岔道不久,他又拐上另一条岔道,随后是下一条。路面每况愈下,到处都是石块。
他用尽浑身解数穿行其间。与此同时,路面高低起伏如同汹涌的海浪,他的视线大大受阻。乌利塞斯神父乘船穿过广阔海域驶向岛屿时,也是这般情景吗?
在他徜徉于海面之际,小路彻底消失了。先前尚能辨认的平整路面被千篇一律、石块密布的荒野取代。小路仿佛一条注入三角洲的河流,将他放逐到无垠的海面。他继续前行,但最终耳边响起了理性的声音,敦促他原路折返。
他掉转车头,但各个方向看上去毫无分别。他糊涂了。四面都是同样的旷野,崎岖、干燥、寂静,目之所及只有银绿色的橄榄树和升腾在空中的大团白云。他迷路了,与世隔绝了。夜晚即将到来。
最终他停车过夜并不是因为迷路,而是出于另一个更为私密的理由:寄生虫大军向他的全身发动了总攻,他再也招架不住了。
他在一块高地上停了车,车头轻轻抵住一棵树。树木散发的馥郁芬芳弥漫在空气中,感觉分外温柔。周围没有一丝声响,没有虫鸣,没有鸟叫,没有风声。耳朵捕捉到的唯有他自己的声响。万籁俱寂,他的目光变得敏锐,那些傲立在寒冬石缝中的细弱野花格外夺目。粉红色、浅蓝色、红色、白色——他不知晓它们的品种,却深深为它们的美丽所打动。他深吸一口气。他完全可以想象这片土地曾是传奇的伊比利亚犀牛的最后栖息地。它们在此间漫步,自由而狂野。
无论他往哪个方向走,都不见一个人影。他一直希望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再解决他的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了。是时候了。
他回到车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生物,能够忍受这种奇痒。
在用魔力药水扫荡敌人之前,他决定最后一次沉浸在恣意搔痒的畅快之中。
他将十根手指高高举起,指甲黑得发亮。随着一声战士般的怒吼,他投入了战斗。他的手指划过脑袋——头顶、头侧、后颈——然后是胡须浓密的脸和脖子。他的动作快速、猛烈、充满激情。我们为什么会在经历痛苦或快乐的时刻发出动物般的叫声?他不知道,但他发出了动物般的叫声,露出了动物般的表情。他喊道:“啊啊啊啊啊!”然后是“哦哦哦哦哦!”他扔掉外套,解开纽扣,脱掉衬衫,扯下内衣。他向身上和腋下的敌人发起攻击。胯下是瘙痒的重灾区。他松开皮带,把裤子和内裤褪到脚踝处。他用力抓挠毛发茂盛的阴部,手指仿佛动物的爪子。
他何时体验过如此的舒爽?他停手细细回味一阵,又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