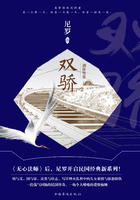
第5章 梦也,命也
雷督理偶尔会爱上个什么人,爱之深恨之切,越爱越恨,所以那感情总是不得善终。他隐约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可是改不了。对着真正亲近的人,他一身的邪火,说恼就恼,说疯就疯,仿佛凡是他所爱的人,都对不起他。
(一)
北京城内的局势,一天紧似一天了。
街头巷尾纷纷地议论,都说这回怕是真的要开战,火车站一带从早到晚总是乱哄哄的,因为已有那胆子小的阔人预备要逃。叶春好先前住在那小门小户里,总觉得天下太平,战争都是外省才有的事情;如今身在这深宅大院里了,反倒惶惶然地坐不住,也许是因为那战争的发动者之一,便是她的丈夫。
张嘉田说是要住在大帅府养伤,其实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跑出去了。叶春好看了他那生龙活虎的劲头,知道他定然是无碍,所以心里也不牵挂他——他日子过得越好,她心里越没有他。她如今心里所装的人,只有一个雷督理。
雷督理如今已经行动自如,从早到晚地不着家。叶春好知道他是在外头做大事,不便干涉,但是一颗心总是为他悬着,怕他一个不小心,又会被敌人行刺或者绑架。
直到这一天,她听到消息,说是山东的卢督理今日登车离京,回济南去了。
卢督理一走,雷督理也回家了。
陪着雷督理一起回来的,是张嘉田。
张嘉田的左胳膊直直地垂着,不敢乱动。当初众人都说他那胳膊被手枪打了个透明窟窿,其实那手枪是一把小小的左轮手枪,威力不大,子弹钻进了肉里去,也并没有真打出个“透明窟窿”来。但张嘉田并没有做解释的打算——透明窟窿就透明窟窿,牺牲越重大,越显出他的忠诚勇毅。否则就凭雷督理那个糨糊脑袋,他若是不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雷督理很可能过不了几天,就把他这份忠勇给淡忘了。
张嘉田确实是感觉雷督理这人有点糊涂,当然不是老糊涂,而是那种天生的糊涂种子,也不是傻,更像是个天资有限的昏君,让人对他好也不是,坏也不是。他刚到雷督理身边一年多,他就看出对方这点本质了,其余人等陪了他十来年,自然应该更了解他。于是张嘉田一边跟着雷督理往书房楼里走,一边心里犯了嘀咕,不知道那些人成天对着雷督理,心里都在琢磨些什么。
然后,他跟着雷督理拐进书房楼下的小客厅里。小客厅垂着水晶帘子,雷督理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来,把两条腿架到了前方的小茶几上:“唉,累啊!”
张嘉田的左胳膊裹着绷带,依然怕碰,所以军装上衣是松松披着的。这时把上衣脱下来往旁边的椅子背上一搭,他满不在乎地,在沙发另一端也坐了下来:“姓卢的动作是快,说跑就跑。”
雷督理向后一靠,嘴上喊累,脸上却是微微笑着的:“城内城外都是我的兵,他敢不跑?”说完这话,他向前欠身,对着茶几上的香烟筒子伸了手。张嘉田会意,起身走去从筒子里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了他,又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摁出火苗给他点燃了香烟。
然后自己也拿了一根香烟,他坐回原位,把烟卷送进了嘴里:“他一跑,总理也哑巴了。”
说完这话,他给自己也点了火儿。深吸了一口喷出烟来,他抬手扇了扇面前的烟雾,然后叼着烟卷扭头去看雷督理,却发现雷督理侧过了脸,也在审视自己。
和雷督理对视了几秒钟,他笑了,取下香烟问道:“干吗?您又瞧我不是好人了?”然后他指了指雷督理那摊在沙发上的右胳膊,“您小心点儿,别烫着。”
雷督理抬起右手,看了看指间夹着的大半截香烟,脸上依然存着笑意:“我什么时候瞧你不是好人了?”
张嘉田笑道:“次数太多了。我看您对别人也不这样,就爱对我来劲,防我像防贼似的。”
雷督理收回目光转向前方,不说话,只是一笑。笑过之后,他正了正脸色,这才又道:“我本以为你最多也就调个两三千人过来,给我撑撑门面也就是了。没想到你一调调来了一万多人,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张嘉田把手中的小半截香烟摁熄在了大烟灰缸里:“大帅,那一万多人,就是我的老本儿了。我怕这边会真开战,就把他们全弄了过来。我知道我那一万多人里头有不少是老弱病残拿不出手的,但看着毕竟也是个人类,即便不能打仗,放那儿充个数,壮壮声势也是好的。”
雷督理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了“人类”这个新词儿,倒是被他逗乐了。而张嘉田这时又问:“大帅,韩伯信下台了,姓卢的跑了,总理也哑巴了。您这回是大获全胜,那个巡阅使,您打算什么时候就职?”
雷督理垂下眼帘,盯着手中香烟的火头:“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不急。”
随即他一转眼珠,望向了张嘉田:“在我就职之前,先把你的军务帮办发表了。”
张嘉田听了这句话,含羞带愧地笑了,像是有些腼腆,其实心中既不羞愧,也不腼腆。他先是救了雷督理的性命,又调来了一万多人的队伍驻扎在城外,为城内的雷督理摇旗呐喊。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功劳。军务帮办,舍他其谁?
两条长腿紧挨着小茶几,拘束着不自在,他也想把两条腿抬起来架上去,也伸展舒服一下。但是他管住了自己的双腿,只给自己换了个坐姿。
“军务帮办……”他沉吟了一下,忽然抬眼对着雷督理笑道,“大帅,这可不是我向您要官,是您自愿给我的。等会儿您回过味儿了,可别又拿脚踹我。”
雷督理一怔:“我什么时候踹你了?”
“去年我刚到您身边的时候,有一次,您硬说我是想跟您要官儿当,一脚把我踹了个大跟头。”
雷督理愣了愣,然后笑了:“他妈的,你还记我的仇?”然后他抬起一条腿作势要踹他,“你要是怀念的话,我再给你一脚尝尝?”
张嘉田立刻向后一挪,脸上笑嘻嘻的。于是雷督理放下腿,把手里那半截香烟向他一掷:“你往哪儿躲?”
半截香烟落在了张嘉田的腿上,张嘉田手疾眼快地把它捡了起来,总算没有被它烫着——雷督理就是这点讨厌,没轻没重的,和这种人相处,一定要和他平起平坐才行,否则就是“伴君如伴虎”。张嘉田捏着那半截烟卷,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去年那个被雷督理一枪打爆了脑袋的严清章——如果他和严清章一样,从小也是跟着雷督理一起长大的,那么到了如今,怕是也要被压迫成雷督理的仇敌了。
可是……
“可是”后头的下文,他不愿去想,眼看雷督理窝在沙发上,两条腿越伸越长,他便站了起来:“大帅,您歇着吧,我回家去了。”
雷督理抬头看他:“回家?”然后他反应过来,“我总记着你是我家的人,忘了你自己也还有个家。”他向外挥了挥手,“去吧。”
张嘉田转身拿起椅背上的军装,抡起来往肩膀上一搭,然后对着雷督理一立正一敬礼,又一笑:“走了。”
礼行得不正经,话说得也没规矩,他故意的,故意地也想试探试探雷督理。雷督理没有恼,只向外又一挥手,懒洋洋地撵他。
这人对他好起来,也是真的好,所以他对他再恼再怨再有意见,后头也总要跟着个余音袅袅的“可是”。
张嘉田回了自己的家。
到家之后他饿了,让勤务兵从胡同口的面馆里端了一碗热汤面回来吃,一碗面吃完了,他刚想端起大碗再喝两口汤,白雪峰忽然到来。
白雪峰见了他,笑得像要开花似的,并且拱手抱拳,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帮办大人,恭喜恭喜!”
张嘉田放下大碗,没起来,只说:“老白,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咱们都是兄弟,哪儿又来了个大人?你不把我当兄弟看啦?”
白雪峰立刻放下了手:“我的帮办大人,不是我凑热闹,我这道喜,是有缘故的。”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又笑了,“大帅说了,这房子实在不配您现在的身份。他另在什锦胡同那边儿拨了一处好宅子给您,请您即刻迁过去。所以啊,我这一趟来,向您道的是乔迁之喜。”
张嘉田听了这话,却是做了个虚怀若谷的样子:“唉,我就是光棍一个人,在哪儿住不是住?大帅也真是太费心了。”
白雪峰笑道:“大帅是把帮办当成家里人看待的,自然处处都想着您。”
张嘉田瞪着眼睛一指白雪峰:“你再一口一个帮办的,我起来揍你!”
白雪峰笑着摆手:“好好好,我不说了,我还叫你张师长,成不成?我的张师长,你只要把你手里的金银细软收拾出来就好,那边宅子已经有人布置去了,一切都是现成的,您今晚搬过去也行,明天也行。”
张嘉田嗍了嗍筷子头:“搬家不能悄悄地搬,得热闹热闹。明天吧!明天我回府里一趟,一是谢谢大帅,二是请大帅到我那新家里坐一坐,我再请个戏班子,敲锣打鼓地唱一夜。”
白雪峰说道:“戏、酒的事情,你都不用管,这个我最会操办。我派几个人过你那里去,一天之内,酒席和戏班子都能给你张罗齐了。”
说完这话,他匆匆走了,张嘉田没多挽留。对于白雪峰其人,他向来是挺友好,也向来是看不起。白雪峰这人没出息,在雷督理身边干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只是个副官长,并且不是什么有实权的副官长。张嘉田暗地里把这人当成了风向标来看——雷督理看他顺眼的时候,白雪峰见了他,必定也是满面春风。
“搬家搬家。”他把大碗一推,自言自语,“你当督理太太,我当帮办大人。多好,多好!”
然后他站起身来,魔怔了似的,又自己嘀咕:“帮办大人,搬家搬家。”
(二)
翌日上午,张嘉田进了这雷督理赠送的宅院,背着手内外溜达了一圈,耗费了大半个时辰。
这宅子本是前朝一位遗老的私宅,雷督理在前些年,有一阵子很好赌,并且赌运很不错,在牌桌上把这处宅子赢了过来,赢过来了,却又没什么用处,便放在那里空置着。还是叶春好到了他身边之后,励精图治,把这大宅院又一点一点地收拾了出来。
这宅子的房屋堪称精致,后头花红柳绿的,也有一个花园子。当初张嘉田做了卫队长,从雷府的仆人房迁去了一处四合院里,都激动得感慨了半天,如今从个四合院搬进了这华丽的府邸里,反倒淡然了。仿佛是拿了一年当十年活,眼界说开阔就开阔了,心气说高就高不可攀了。
有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活得不真实,像是在做梦。但是凭着他的出身和底子,他做梦都梦不到这样高贵的阶级上来,所以这不是梦,这是他的命。背着双手走在一道深深的长廊里,走着走着,他停了下来,背靠着那顶天立地的红漆廊柱,他闭了眼睛,觉着有些眩晕。
梦也罢,命也罢,富贵与权势都来得太突然了,太猛烈了,让他竟然有些消化不了,招架不住。他让随从搬来了一把椅子,然后原地坐下了,挥了挥手,让他们都退到远处去。
四周安静了,只有微弱的凉风吹过。他瘫软在椅子上,细细地听那风声,心里想自己原本只是个赤条条的人,这个人起初是个街头上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后来进入大帅府,成了个小听差,小听差聪明伶俐会巴结,摇身一变成了卫队长,卫队长稀里糊涂地跑去文县,又成了个师长。师长是不好干的,但也干下去了,东拉西扯地弄了些钱,弄了些枪,招了些兵,乱糟糟地凑了上万人马。这上万人马放在文县,单是吃饭,就是个不好解决的大问题,然而偏巧北京城里出了事,这支乱糟糟的队伍就爬上闷罐车,从文县城内转移到了北京城外。
与此同时,师长也立了功,于是又升官,成了帮办,成了现在的他。
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有迹可循的。他当帮办,理所当然。
他是英雄出少年!
双手一拍扶手,他从椅子里弹了起来。昂首挺胸地站直了身体,他背着手,晃着大个子继续往前走。
他是帮办,他手下有一万人,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就驻扎在北京城外。
除了这一万人,他另有余部留在文县,文县也是好地方,四通八达,繁华热闹,兵家必争之地。目前,也归他管。
迎着那么一股似有似无的小凉风,他向前走,越走越快,脸上带着一点微笑,微笑如风,也是似有似无。身后响起窸窸窣窣的脚步声音,是随行的副官和勤务兵跟了上来,一个个的,大气都不敢出,仿佛帮办大人是雪做的,气儿出重了,便要将大人吹化。
张嘉田在宅子里巡视完毕,十分满意。回头便来了雷府,要向雷督理致谢。然而雷督理无影无踪,他一路找来了书房,上楼一瞧,依然是没瞧见雷督理,反而是看到了叶春好。
叶春好正在用小钥匙去锁墙角的铁皮文件柜,见他推门进来了,显然也是一惊:“哟,二哥?”
张嘉田一手握着房门把手,停在门口,进退不得:“春好。”
说完这话,他补了个笑容:“我以为大帅在这儿呢。”
叶春好笑道:“他今天早早地就出门去了,热河的虞都统回承德,他去送送。你要是有要紧的事情找他,就坐下来等等,我猜他一会儿就能回来。”
张嘉田还站在原地,不动:“我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情,就是想来谢谢大帅。那个——你知道吧,大帅送了我一所宅子。”
叶春好一边把小钥匙收进皮包里,一边答道:“我知道的。二哥,你做了帮办,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呢!”
张嘉田听了这话,却是含笑默然了——帮办自然是个大官,可再大也大不过督理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叶春好也还是要选择雷督理做丈夫的,这样一想,这喜事就又显得还不够喜。
于是抬眼注视了叶春好,他自作主张地换了话题:“你……好像胖回来了一点儿。”
叶春好一直在观察着他——从他离开北京去了文县开始,她每次见他,都觉得他像是长大了一点,又像是苍老了一点,那苍老是印在眼睛里的,是看过了很多很多的人、想过了很多很多的心事才能熬出来的眼神。她一直活在这风平浪静的北京城里,头上一直有着雷督理的庇护,可单只是因为管着大大小小的许多事务,便常有心力交瘁之感。张嘉田那样一个无忧无虑、无知无识的小伙子,忽然跑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外县,面对着一帮老奸巨猾的豺狼虎豹,他要耗去多少心血方有今天的成绩,可想而知。
“我就是这样。”她眼睛看着他,心里有叹息,语气却是若无其事,并且还带着一点客气的笑意,“少吃几口就瘦了,多吃几口又胖回来。倒是二哥,这些天真是辛苦了。”
张嘉田也笑了一下:“我不白辛苦。”然后他又说道,“晚上我请客,搬家嘛,总得热闹一场。我想请大帅到我那里坐坐,你也去吧,好不好?”
“好不好”三个字让他说得很轻柔,是试试探探地要和她打个商量,有一点恳求的意思。
叶春好听出来了,但是装听不出,只笑着点头:“好,你这回搬家,不同于往日的搬家,应该大大地庆祝一次。只是你有没有找人帮忙?请客这种事情,说着简单,办起来就烦琐了,照理来讲,就应该挪到明晚去请,这样时间上也从容些——”话说到这里,她猛地停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自己真是嘴碎,人家搬家请个客,哪里就轮到自己唠唠叨叨了呢?
张嘉田看她笑,也跟着笑了笑,像是瞧出了她的那点儿尴尬:“老白替我办,昨天就说好了,酒席和戏班子都归他管。”
叶春好点头笑道:“那就妥了。”
话到这里,两人似是谈到了山穷水尽。叶春好搭讪着把那写字台上的笔筒挪了挪,然后抬头说道:“我得走了,我……”
张嘉田听了前四个字,便下意识地一侧身,要给她让路。叶春好见了,便迈步走了出去——走了几步之后,她回头看张嘉田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便带着微笑说道:“二哥不是要等大帅吗?”
张嘉田恍然大悟:“啊——对,我得等大帅。”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楼梯口,叶春好抬手扶着楼梯扶手,回头含笑说道:“你到楼下小客厅里等着也成,留在楼上屋子里等着也成。你不是外人,就自己随便吧,我得出一趟门去,就不招待你了。”
张嘉田认为叶春好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理,所以连连点头:“好好好,行行行,你忙你的,我——”
这句话又没说完,因为他目光一转,忽然发现楼梯下方站着雷督理。叶春好这时把脸转向前方,也愣了一下。
雷督理没穿外衣,是衬衫军裤的打扮,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孤零零、冷飕飕地站在楼梯前,他像不认识了他俩似的,睁着大眼睛直勾勾地向上看着他们。还是叶春好先唤了他一声“宇霆”,他才眨了一下眼睛。
在这位丈夫面前,叶春好不知为何,永远有种做贼心虚的恐惧。当即把张嘉田抛到脑后,她笑微微地走下楼去,说道:“你回来得正好,二哥等着你呢。”
这话说完,楼外气喘吁吁地又走进来一个人,却是林子枫。林子枫一手提着一只公文包,另一条胳膊上搭着雷督理的军装上衣,外头说是春天,其实已经有了夏天的阳光和温度,林子枫热汗涔涔地追了进来,偏又是个高个子,就像一盏路灯似的,只是不放光明,放的是热力与汗气。有他比着,越发显得雷督理“清凉无汗”,似是个无可救药的病人,也似是个得了什么道的小仙。
进入楼内之后,他抬头看见叶春好和张嘉田,没说什么,只一点头。雷督理抽了抽鼻子,不知道是被什么气味刺激得清醒了过来,开口向上问道:“等我有事?”
张嘉田这才迈步下了楼,脸上换了喜气洋洋的笑容:“大帅,我这么早跑过来找您,有两件事。一是来谢谢您,您赏我的那大宅子,真是气派极了。我进去一瞧,简直吓了一跳!第二件事呢,就是我等不得了,今晚就搬家。搬家得请客,您是我心里天字第一号的贵客,我来请您晚上到我那新家里坐坐,您赏不赏我这个脸?”
话说完了,他人也走到了雷督理面前,可雷督理背着手,似笑非笑地仰脸看着他,却是不说话。
张嘉田和他对视了片刻,忽然明白过来,连忙一弯腰,小声笑问道:“大帅,好啦,您给我句话,赏不赏脸啊?”
他这一弯腰,便把自己的高度降低了,雷督理垂了眼帘看他,这才答了一个字:“赏。”
张嘉田笑着抬了头:“好,谢谢大帅。您去,太太也去。”然后他抬头去看林子枫,“老林,我不给你下帖子了,不是我怠慢你,一来咱们是好朋友,可以不讲那个虚礼,二来是我根本没帖子,我看完房子就跑过来了。”
林子枫听他叫自己“老林”,感觉十分刺耳,但是没法挑理,只能点头答应着。张嘉田这时又道:“老林,你家里要是有女眷,也一并带来吧!我那儿没别的可玩,但是老白派人帮我请戏班子去了,说是能有小兰芳,这可值得一看。”
林子枫想了一想,然后答道:“那我带舍妹过去。”
张嘉田笑呵呵地答道:“好极了。”然后他转向雷督理,“大帅,那我告辞了。趁着天早,我回家再张罗张罗去。”
雷督理点点头:“去吧。”
张嘉田再没看叶春好,自己颠颠地跑出去了。叶春好不便紧随着他往外走,只得停下来,因见雷督理不住地打量着自己,便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我怎么了,要你这样一个劲儿地瞧?”
雷督理答道:“你和他站在楼梯上,看着倒是很好看。”
叶春好听了这话,不明所以:“好看?什么好看?”
随即,她品出了这话里的酸味,当着林子枫的面,她脸色不变,只抬手轻轻一打雷督理的肩膀,做了个打情骂俏的活泼样子:“我不好看,还是你好看!”
不等雷督理回答,她拔腿就走,且走且笑道:“我要出门去,可不和你胡闹了。”
(三)
叶春好出门上了汽车,一只手狠狠摁着心口那里,就觉着自己的心脏紧缩成了一只坚硬的小拳头,不是伤心,也不是得了什么心脏病,完全只是心理受了刺激,反应到了肉体上。
这毛病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她说不清楚,或许就是由她和雷督理的那一场冷战而起。她没亲人,丈夫就是她唯一的亲人,偏她和这丈夫还是自由恋爱结婚,她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他。越爱他,越关怀他,越把一颗真心给他,越受了他的制。他说翻脸就翻脸,说走就走,她原本以为自己是了解他的,事到如今,她才发现自己其实连他的脾气都没摸清。
没摸清,也摸不清。表面上,她是不怕他的,可私底下,她已经养成了对他察言观色的习惯——她那个娘家虽然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可在太平时候,还是一团和气的。她没有家庭斗争的经验,纵是有了那个经验,也没有那个习惯和精力。所以她只盼着雷督理不要闹,如果一定要闹,也不要大闹。
她也真是怕了他了。
汽车开到了俱乐部后边,她下车进了账房。先前她做叶秘书的时候,这账房里的先生们就已经对她很是恭敬,如今她从叶秘书进化成了雷太太,先生们越发把她当成皇后那样来对待。她犯不上对这些老狐狸耍威风,先前是怎样的做派,如今还是怎样。把这一个月的账本子翻看了一遍,她看出了一点小小的纰漏,但是只做不知。做事不能太绝、太清楚,这是她渐渐悟出的道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然后离了账房,她又去见了天津大洋公司驻京办事处的经理,闲谈了几句。一边谈着,她一边忽然生出一个感想:雷督理并不禁止她与男子接触,也允许她在社会上活动奔走,自己若是当众谴责雷督理封建的话,那是绝对不会有人同情的。
过了中午,她回了家。回家之后,也没敢张罗着往张家去——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吧,她全听雷督理的。
她犯不上为了个张嘉田,去往丈夫的枪口上撞。
凉凉快快地往一张躺椅上一躺,她喝茶望天,自觉着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硬拳头似的心脏慢慢松弛柔软了,她心里还存着许多件要紧的心事,愉快是不能够了,但身体终究是舒服了些许。
舒服了没有几分钟,她忽然一挺身坐起来,使唤小丫头道:“把我的皮包拿过来。”
小丫头立刻跑去取来了她的小皮包。她打开皮包向内摸了摸,摸到一把小钥匙,又摸到了一只小药瓶。把药瓶拿出来瞧了又瞧,她看上面贴着标签,标签上印着英文,每个单词都是长长的,让她完全认不出。于是她攥着药瓶跑上楼去,开始去查英文词典。
她不是博学之士,查词典查出了一头的热汗,正在数着页码翻来翻去之时,房门一开,却是雷督理进来了。
雷督理是悄悄地走进来的,等她察觉到时,他已经紧挨着她站住了。目光从那个小药瓶转移到了她的脸上,他不说话,对她单只是看。而她仓皇地回了头,先前松弛的心脏猛然又揪紧了,紧得让她几乎感到了疼痛。
“吓我一跳!”她的语气并不很惊,但脸上也没来得及放出微笑。
雷督理伸手拿起那只小药瓶,掂了掂,药瓶是空的,没什么分量:“怎么还学会搜查我的柜子了?”
叶春好方才忘记了坐下,一直是在弯着腰翻书,这时便直起身来答道:“我不是搜查你的柜子,我是去找你的印章来用,结果看到你那柜子里锁着这么一大盒药瓶。”
雷督理笑了一下:“然后呢?”
叶春好对他是问心无愧的,所以不管他怎样阴阳怪气,她只是以着一贯的态度说话:“我平时也没听说你有什么需要长期服药的病,就拿了个空瓶子出来,想要查个究竟。”
“查明白了吗?”
叶春好停顿了一下,脸上隐隐地泛出了一点红色:“我没觉得你有这方面的毛病,我一直觉得你很健康。”
雷督理将两只手插进裤兜里,微微俯身偏着脸,去看她的眼睛:“你真这么觉得?”
叶春好迎着他的目光说道:“你好端端的,却要吃这种药,我觉得你这行为,真是近乎于无知兼无聊了。”
雷督理直起了身,对着她摇了摇头:“我不是没事找事,吃了药来玩儿。我是真的感觉自己——”
说到这里,他皱了眉毛:“玛丽是不肯给我生,那就不用提了,可那个林燕侬为什么也——”
这两句话,都让他说得有头没尾,但叶春好听明白了。
“兴许就是因为你乱吃药,耽误了呢!”她抓住雷督理的一只手,正色说道,“若是我们命中有儿女的,那怎么样都会有,若是没有,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不许你再乱吃药了。除去生儿育女的事情不谈,其余的……”说到这里,她顿了顿,脸更红了,“其余的……对我来讲……”
斟酌来斟酌去,她还是觉得下文那话无法出口,索性一转身背对了他:“不说了,反正夫妻感情好不好,在乎于心,和那事没有关系,你就好好地听我这一句话吧!”
话音落下,她等了片刻,却是没有等到雷督理的回答。忍不住转过身来,她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摇了摇:“宇霆?”
雷督理向她一笑,笑过之后,从她手中把手抽了出来:“你少管我的事。”
说完这话,他转身向外走去。
叶春好看着他的背影,眼睁睁地看,知道自己今天又把他得罪了——自己一点坏心都没有,完全是要为了他好,然而还是把他得罪了。
雷督理下午冷冷淡淡地走了,可是到了晚上,他携着叶春好往张宅去时,不知是谁把他哄高兴了,他瞧着叶春好,脸上又有了那真心实意的笑容——是不是真的笑,叶春好一眼就能瞧出来。
叶春好也不奢望着他能“听话”了,只要瞧见他这样兴致勃勃的,她就也跟着轻松欢喜了起来。及至进了张宅的门,雷督理立刻就被一盆火似的张嘉田笼络了过去,她看在眼里,也觉得非常好,甚至有了闲心问道:“二哥,小兰芳真来了吗?”
张嘉田连连点头,然后对着她和雷督理笑道:“不只是小兰芳,还有好几个名角儿。正好,这花园子里有现成的戏台,上下把电灯一装,亮堂堂的,比正经戏园子还好。”
叶春好听到这里,只是微笑。而雷督理对于名伶的兴趣并不大,单是一边往宅子里走,一边留意观察着这宅子里的人。
宅子里的人,都是张嘉田的人——张嘉田从文县调过来的人。
这时候,魏成高参谋长带着一群有头有脸的军官闻讯赶了出来,瞬间就把雷督理团团围了住。除此之外,政界的名流们落后一步,这时也迎上来了,此起彼伏地向雷大帅问候。雷督理对着四面八方含笑颔首。而叶春好虽然并不怕男人,这时却也不动声色地悄悄退出了人群——政界名流之内,不知是哪一位吃了蒜,气味实在是熏人得很。
这些人寒暄笑语,是乱哄哄的,及至到了晚宴时节,依然是乱纷纷,幸而是乱中有序,并非一乱到底。及至众人吃饱喝足了,便走去花园子里看戏。戏台前方摆了几副特别精致些的桌椅,尤其是正中央的桌子后放了一架长沙发,分外地柔软舒适,显然是雷督理夫妇的座位。
张嘉田引着雷督理走过来坐下了,一手扶着沙发靠背,他俯下身正要说话,眼角余光忽然瞄到身旁走来个人,便抬头问道:“什么事?”
那人是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一脸红疙瘩,倒是军装笔挺,垂手站着,瞧着也挺有规矩。上前一步凑到张嘉田身边,他开口先唤了一声“干爹”,然后才嘁嘁喳喳地说起话来,倒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张嘉田听完了,随口发话打发了他走,然后俯身要继续对雷督理说话,雷督理却是抬头向他笑问:“你才多大,给人家做干爹?”
张嘉田也笑了:“我年纪是不大,可架不住我官大啊!您忘啦?那时候我还想给您当个干儿子呢!”
雷督理饶有兴致地看他:“记得,我驳回了。怎么,现在还想再试试?”
张嘉田摇了头:“不了,您这岁数摆在这儿呢,我就是认了您做爹,外人瞧着也不像,还兴许被人传成笑话。”
雷督理和颜悦色地反问:“笑话?谁敢笑话帮办大人?”
张嘉田乐不可支地抬手一指雷督理:“甭说别人,现在您自己就已经笑了。”
从来没人敢这么用手直指着雷督理的脸,叶春好在一旁看着,身不由己地就向上一起——起到一半,她顺手理了理裙子下摆,又坐了回去,伸手去摸茶壶:“二哥,这茶怎么是凉的?”
张嘉田走去端起茶壶,手指关节碰触到了壶身,烫得他手一抖。但他没言语,甚至也没看叶春好,只笑呵呵地答道:“我让人换一壶去!”
他走了,留下雷督理扭头望向叶春好,低声说道:“你倒是很会替他遮掩。”
叶春好来时饿了,方才在席上没少吃喝,胃里沉甸甸的都是饮食。此刻听了雷督理这句话,她只觉着心中一翻腾,但是脸上依然淡淡的没脾气:“怎么又怪起我了?我遮掩什么了?”
这话说完,她像忍无可忍了似的,把脸转向了那金碧辉煌的戏台,就觉着腹中混乱,胃部也开始隐隐作痛了。
(四)
叶春好本来并不懂戏,兴冲冲地来看,也主要是存了一份看热闹的心思。热闹这种东西,有闲情逸致时自然是爱看的,可她现在暗暗用手捂了胃部,也说不清自己是个什么情绪,总之像被自家丈夫吓出了心病似的,他不阴不阳地甩给了她一句话,她的身心便都承受不住了。
台上锣鼓喧天地热闹着,花蝴蝶子似的名伶穿着戏装满台飞,越发看得她头晕目眩。忽然抬手捂了嘴,她紧闭了眼睛定了定神,然后勉强对雷督理笑道:“我要离开一下,好像是方才吃得不对劲了。”
雷督理盯着戏台,微微一点头。
她见了他这个态度,也来不及计较,转身便走。雷督理眼睛看着名伶,耳朵听着她的脚步声音,心想她终究还是关心张嘉田。张嘉田没规矩,用手指了自己的脸,自己还没怎样,她先紧张了——为什么紧张?是不是怕自己怪罪张嘉田?
她在心里,护着他呢!
雷督理偶尔会爱上个什么人,爱之深恨之切,越爱越恨,所以那感情总是不得善终。他隐约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可是改不了。对着真正亲近的人,他一身的邪火,说恼就恼,说疯就疯,仿佛凡是他所爱的人,都对不起他。
怎么着都是对不起他,所以他委屈透了。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茶,他没尝出滋味来,也不知道是什么茶。
身边有个人,来回地活动,一时来了,一时走了,一时像个游魂似的,无声无息地又来了。他终于忍不住扭过头去,瞧见了个洋装打扮的小姑娘。小姑娘正在戏台正前方这几处座位间来回地寻觅着什么,冷不丁地被雷督理盯住了,她也是一怔,紧接着向他一鞠躬:“大帅好。”
雷督理认出了她:“在找人?”
“嗯。”她直起腰,点点头,小脸苍白的,“我找我哥哥呢。他让我到这儿来找他,可我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他。”
雷督理转身去问不远处的白雪峰:“子枫呢?怎么把他妹妹扔这儿不管了?”
白雪峰靠边坐着,听了这话,立刻站起来答道:“回大帅的话,我刚瞧见他被魏参谋长拽走了。”
雷督理答应了一声,转向前方继续看戏——看了几秒钟,忽然反应过来,回头又去看林胜男,就见林胜男孤零零地站在原地,显然是没主意了。察觉到了雷督理的目光,她看了他一眼,然后立刻垂下头去,转身要往一旁的人丛里钻。
雷督理忽然觉得这女孩子是个小可怜儿,便对着她一招手:“胜男。”
他叫林子枫为子枫,对待林子枫的妹妹林胜男,他自然也就不假思索地喊了一声“胜男”。可林胜男听在耳中,却是有一点惊,没想到雷督理会这样亲近地呼唤自己。回头望着雷督理,她看见他向自己又一招手,分明是在示意自己过去。
她环顾四周,还是没有看到哥哥的影子,自觉着无处可去,只好垂头走到了雷督理身前:“大帅。”
雷督理一指身边的空位:“坐这儿等着吧。你哥哥迟早得过来。”
然而林胜男迟疑着摇了摇头,并不肯动。于是雷督理莫名其妙:“怎么?还有别的事?”
林胜男小声答道:“这是大帅太太的位子,我坐了,太太回来可坐哪儿呢?”
她心里有什么,嘴里就如实地说了出来,却没想到大帅此刻正对太太含恨,听了她这番话,雷督理越发来劲了,索性抓着她的手往身旁一摁:“不管她,你坐你的。”
林胜男吓了一跳,坐下之后立刻缩回了手。可坐着的确是比站着舒服多了,沙发也的确是比那硬木椅子舒服多了,坐在这里,一抬头就无遮无拦地看着戏台,看得清楚,听得真切,也真是一种享受。
看着看着,台上“咚”的一声,她也跟着“哟”了一声。“哟”过之后,她见雷督理闻声望向了自己,就小声解释道:“我看台上那人忽然跳到了桌子上,吃了一惊。”
雷督理答道:“那桌子代表的是山,你看着他是上了桌子,其实这在戏里,演的是他上了山。”
林胜男点了点头,因为心里原本就知道他这人是很和蔼的,如今共坐了片刻,那种紧张劲儿也退了,便有了勇气同他讲话:“那这人打着旗子从台上跑过去,又是什么意思呢?”
雷督理答道:“那旗子代表的是风,他这么扛旗走一圈,意思就是刮了一阵风。”
林胜男很认真地“哦”了一声,点了点头。雷督理看她是一副很受教的样子,心里倒有些愉快,便问:“你哥哥很少带你去看戏?”
林胜男有点害羞地笑了:“是的,他说戏园子太乱,空气也不好,不许我去。”
雷督理听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一件小小的旧事:“我让你没事时到我家里玩玩,怎么不见你来?”
林胜男支吾了几声,声音细细的,像是雏鸟,弱得连句整话都答不出,幸而旁边有人替她做了回答:“大帅,舍妹有点小孩子脾气,您虽然是这么说了,可她还是胆子小,不好意思去。”
雷督理一回头,看见了林子枫:“你跑哪儿去了?”
林子枫答道:“刚和参谋长在一起。”
“妹妹都不要了?”
林子枫笑了笑,伸手一拍林胜男的肩膀:“起来吧,别再打扰大帅看戏了。”
林胜男刚要起身,雷督理发了话:“坐着吧!要不然我也是一个人——全他妈的躲着我!嘉田呢?”
林子枫的手方才拍了妹妹的肩膀,这时也没有收回,而是顺势把妹妹又摁住了:“不知道帮办在哪里,我方才也没有看见他。”
他既是一问三不知,雷督理便不耐烦地向后摆摆手。林子枫见势,也不言语,直接退到了白雪峰那一桌,坐了下来。白雪峰给他抓了一把瓜子,但他不爱吃这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只守着一杯清茶慢慢喝,偶尔向妹妹的方向扫一眼——妹妹和雷督理已经谈起来了,当然,妹妹还带着一身孩子气,一定说不出什么漂亮的话来,不过女子只要是有着青春与美貌,那么稍微蠢笨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
他希望雷督理火速移情别恋,叶春好那副西太后式的专横样子,他实在是一眼也看不下去了。
紧接着,他又想:“她不是也来了吗?现在跑到哪里去了?”
想到这里,他就去问了白雪峰:“怎么不见太太?”
白雪峰坐在这个好位置上,也不知道是为了看戏还是为了吃,嘴一直不闲着,听了林子枫的问话,他还得先喝一口热茶把口腔冲刷一下,然后才能腾出唇舌回答:“大概是去了化妆室、卫生间一类的地方,不清楚。”
林子枫点了点头,又想了想,然后也不说话,直接起身又走了。
叶春好并没有往远了走,还在这花园子里,只不过是迷了路。
她胸中烦恶,本意确实是想找到卫生间,进去洗一把脸,振奋一下。然而她对这宅子的格局完全陌生,眼前又没个仆役听差,想问路都不能够。偏在这时,迎面有几个人走了过来,为首一人步履匆匆,却是张嘉田。
张嘉田抬头见了她,明显就是一愣,“太太”也不叫了,开口就问:“你怎么一个人走到这里来了?”
叶春好勉强笑了一下,心想自己可不能和二哥多说话,万一让哪个长舌头的看见了告诉宇霆,回家又是一场闹。
她心里想得清楚,行动上更是贯彻得彻底,一言不发,捂着嘴就跑到了路旁草地上——不跑不行了,单手扶着一株细瘦小树,她一低头,便是呕吐出了一口。
张嘉田看了,一大步也迈了过来,叶春好接二连三地大吐起来,怕弄脏了他的裤子、皮鞋,伸了一只手想要推他远离,然而他全然不在乎,只急急地回头吩咐:“去,拿热毛巾过来,快点!”
叶春好自恃身体好,肠胃也是铁打的一般,万没想到今天会如此脆弱失态。上气不接下气地将晚餐饮食尽数吐了个干净,她累得面红耳赤,依稀觉得有热毛巾递过来了,她接过毛巾擦了擦脸,非常地不好意思:“我这两天肠胃不舒服,方才大概是……”她不好说自己是吃多了,所以慢慢地直起腰来,她终究也没说出个缘由来。
她不说,张嘉田也没追问,只道:“夜里风凉,那戏你就别看了,进屋子里歇歇吧!”
叶春好刚想推辞,可是眼冒金星地晃了几晃,她很识相地把那客气话收了回去。
张嘉田把叶春好领进了一间小客厅里。
叶春好重新洗了脸,漱了口,恢复了从容的仪态,只是眼圈有点红,是方才面红耳赤的残影。在那明亮灯光下,她抬眼看着张嘉田,看他放着好好的沙发不坐,非要骑在沙发扶手上,坐没坐相,是个野小子。
野小子和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问她:“你是不是病了?”
她摇摇头:“我没事。”
野小子默然了,双手扳着沙发扶手的一端,越发显得胳膊很长,腿也很长,站起来不知道会有多高。低头看着地毯出了会儿神,他忽然望着叶春好,又道:“府里不是有现成的大夫吗?你哪儿不舒服了,就叫他们给你瞧瞧。你自己的身体,就得你自己当心。别人……也没法儿管你。”
叶春好点了点头:“是,我知道。”
张嘉田又道:“你要是喜欢看戏,我过两天把那帮唱戏的再叫过来,给你们重唱一遍。”
“我其实也不懂戏。”叶春好低声说,“只不过是凑热闹而已。人家说谁是名伶,我就好奇起来,其实看不看都成的,我并没有那种戏瘾。”
张嘉田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挪到沙发上坐下了,把两只手端端正正地放到了大腿上:“多谢你今天提醒我,我这人不懂规矩,总是……没礼貌。”
叶春好想要扼杀掉他对自己的所有情意,所以微微笑着,不肯承认自己的目的是要“提醒他”。
“我是怕二哥一时疏忽,惹得大帅不痛快。”她说道,“大帅现在为了国家大事,已经是殚精竭虑了,今晚既是来玩的,那就让他称心如意地乐一晚上吧。”
张嘉田点了点头:“是,你说得对。”
然后他状似无意地抬了头:“大帅今晚上大概是乐的了,你呢?”
叶春好站了起来,脸上依然是微笑着的:“我也很好。”
张嘉田看着她那张苍白的面孔,又问了一次:“真好?”
叶春好移开目光,轻声答道:“好。”
张嘉田也站了起来:“好,你好就好。”
叶春好下意识地迈步要往外走,走了几步,却又不想再走——若是这样一路地走下去,就要走回到雷督理身边了。
她不知道丈夫正以怎样的面目和心情等待着自己,她不是怕,她只是有点不想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