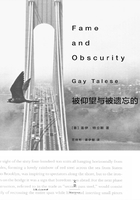
第5章 纽约——一位猎奇者的足迹(4)
这就是她们在纽约城里的工作——她们是那些有着自己的工会组织的1.2万名清洁女工。她们每天夜里要抚慰1000英尺的地板和沉睡的电话,轻轻擦拭桌面上别的女人的照片。傍晚6点,200名清洁女工脚蹬平底鞋,身着农妇穿的那种蓝布衣,迅速地奔向帝国大厦的3000个房间;她们每年能在那里的地上发现总计约5000美元的钞票和硬币,有时在家具后还会发现隐匿的偷情者。但她们都非常忠于职守,把拾到的钱全部上交,并且把那些偷情者报告给警卫——可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什么感谢。
晚上7点半,350名清洁工已进入洛克菲勒中心。这座楼里的所有废纸在被倒入筐子后,都得在仓库里保存48小时,每个吸尘器也要在12小时后再清理。这种做法对珠宝商找回他们丢失的金粉、钻戒及小宝石等物品非常奏效。
午夜时,几千名清洁工来到华尔街的某个大厅,那里到处是股票自动接收机上使用的纸条。她们干活时小心翼翼,只扫掉在地上的碎纸,不会乱动桌上的任何东西。常常有某些经理故意把碎纸扔在桌面边缘,试探清洁女工是否照章办事。
这些清洁工大多是乌克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她们每周工作35小时,最低起薪只有54.95美元。她们干这份工作,或是为支撑一个大家庭,或是为挣钱补贴微薄的离婚赡养费,或是为在夜里能离开家。然而,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往往非常保密,只告诉邻居自己做的是些夜间职员工作。
与那些白天上班时不停抽烟、一点儿也不体谅清洁工的人一样,她们的子女有时对清洁工的工作也知之甚少。那些白天在这里工作的人,早上一上班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往烟灰缸里弹烟灰,往纸篓中扔报纸,把这个地方搅得乌烟瘴气,目的好像就是让那些夜晚出动的拿着废物筐的无声无息的清洁工来收拾。
每逢周五和周六夜晚,一些吉卜赛人、乞丐和小偷就会汇集在艾伦街133号,等待每周一次到曼哈顿最后一家公共澡堂洗澡的机会。对光顾过那里的成千上万的其他客人来讲,他们觉得公共澡堂简直是一座四壁镶满瓷砖的泰姬陵。
似乎所有来到澡堂里的人都很平静。他们在一排排的椅子上低头坐着,等待进入可供90个人使用的淋浴间。这里的规矩是,如果自带毛巾和香皂,洗澡不花钱,否则得交25美分押金;如果不偷走毛巾,25美分押金还会如数退还。
每年有130多万人在艾伦街公共澡堂洗澡。他们中有退役的拳击手,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以及那些年轻时有些姿色、现在却人老珠黄的干瘪老妪。
在这里每人只有20分钟的洗澡时间,时间一到,澡堂工作人员就会摇铃,在雾蒙蒙的浴室里大喊大叫,直到人们全部出来,重新穿上他们那些肮脏的衣服。
在纽约城里,每天有9万人拨打WE 6-1212,询问天气预报;有7万人拨ME 7-1212,查询时间;有65万人因为不知该打什么电话而拨打411。查号员需要用15秒查到一个电话号码。她们在连续工作两个小时,查询了130多个电话后,就可以休息15分钟,抽支烟或喝杯咖啡。即使下班后,她仍吐字清晰。当然,有时她真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不再这样讲“5——7——9——”,但却很难做到。
假如人们能自己查一下号码……
当她把手里的烟头用力掷出,又到拨号台前继续查号时,她在想,假如人们能够自己查号,她的工作就会容易得多。她继续为纽约的410万台电话及那些害怕电话号码簿的变态狂查号。这些人或是需要查询电话号码,或是需要有事问询,或是因为孤单想找人聊天,或是只想与接线员约会,引诱她……
但是他们不愿自己去查曼哈顿电话号码簿,那里面有78万个名字,1830页,重达五磅,厚得即使是查尔斯·阿特拉斯和维克·唐尼这样的大力士现在也不愿再撕开它们了。这两位大力士已厌倦了这种游戏,据说还问过:“谁会需要这种东西?”
谁会要这些每年都印刷179.5万册的曼哈顿电话号码簿呢?
其中四分之一在华尔街被丢弃、弄坏或撕烂,被人们同打印纸、手纸一起从摩天大楼里扔出来,砸在那些为某个明星捧场沿着下百老汇到市政大厅的大街游行的名流身上。
另外四分之三每年都被收废纸的收走了。他们把电话号码簿一页一页地翻一遍,试图找到遗忘在里面的情书、邮票、保险单、领带和钱,然后再把它们装船,沿哈德孙河运往一家纸板厂。在那里,这些电话号码簿被化成纸浆,制成洗衣店使用的熨衣板、装鸡蛋的盒子、平装书的封皮,以及那些无论查不查电话的纽约人身边一些好看但不值钱的东西。
“先生,擦皮鞋?”
“先生,擦皮鞋?”
“嘿,先生,擦擦皮鞋吧!”
当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时,人们能看到纽约城里到处游动着擦鞋匠。他们一字排开,像猎鹰一样地争抢生意。此时,你走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全部是这样的喊声——这些擦鞋匠有时躲在角落里,有时蹲在马路边,有时在行人中转悠,嘴里低声吆喝着:“擦皮鞋!擦皮鞋!”就像那些兜售黄色画片的小贩一样。
纽约城里有800个无证经营的擦鞋匠,他们最怕看到警察,因此必须迅速完活儿。他们比那些室内擦鞋匠更可能把鞋油弄到你的袜子上。纽约城里约有1500个在室内工作的擦鞋匠,他们一般分布在商店和旅馆里,有的擦鞋匠竟像皇室人员一样,坐在华丽的高脚椅上,等待客人的惠顾。
那些年老的且有一定地位的擦鞋匠也不像那些街上的年轻孩子一样无名无姓,他们常常会取得很高的成就。像擦鞋大王戴维,能在布朗克斯区地方法院干活;或已故的比亚乔·韦卢兹,在羔羊倶乐部[8]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墨菲的擦鞋匠;还有查理,那个乘消防云梯车的擦鞋匠消防员;还有詹姆斯·瑞那尔蒂,那个可以用27种语言说“擦皮鞋吗?”、在联合国大厦工作的擦鞋匠。有时他们会变得像“丝帽托尼”一样出名。托尼是在百老汇和运河街干活儿的一位衣冠楚楚的擦鞋匠,他的眼睛不会放过面前走过的每一双脏皮鞋。人们不禁怀疑,他其实像这座城市里的许多神秘人物一样非常有钱。
但是,谁也不可能知道普通擦鞋匠每周挣多少钱。他们通常有自己的一个守口如瓶的小圈子。擦完鞋时,他们会敲一下顾客的鞋跟或脚踝,宣告他们工作的完成。但他们不会抬起头来讲话。
不管怎么讲,最近纽约地铁车站里擦皮鞋的价格已涨到了20美分,但在大多数地方仍是15美分。在第四十九街和百老汇交汇处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他的擦鞋箱上挂出了“擦鞋5美分,税20美分——总计25美分”的招牌。然而,他遇到了来自第三大道另一位年轻擦鞋匠的挑战,这位擦鞋匠举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擦鞋免费——小费25美分”。
作为一个群体而言,酒店擦鞋匠一般是最富有的,他们每周能挣到60至80美元。游客和过路人都是他们的好主顾,尽管许多游客经常用旅馆里的毛巾和毯子擦鞋。“他们这样做时我们总能看出来,”阿斯特酒店的一位擦鞋匠说,“那些在旅馆房间或自己家擦鞋的人通常鞋油挤得太多,鞋油都凝固在鞋帮上了,一副邋遢样。”
1957年,阿尔伯特·安娜斯塔西亚在喜来登公园酒店理发时被人枪杀。当时,除安娜斯塔西亚外,理发店中还有11个人——五个理发师,两个顾客,一个修脚师,一个服务员和两个擦鞋匠。对安娜斯塔西亚来讲,这两个擦鞋匠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总是低头擦皮鞋。但这件小事却没逃过记者迈耶·伯格的眼睛。在第二天为《纽约时报》所写的案情报道中,伯格先生这样写道:
“安娜斯塔西亚大约10点15分走进酒店的理发店。他把上衣挂在衣架上,解开了白衬衣的扣子;他全身上下都是黄色——黄色皮鞋(上面的鞋油一看便知不是专业人士打的),黄色外套……”
纽约的擦鞋匠对像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同情。
纽约天热时,女人穿着裙子婀娜漫步,敞篷车的车顶放下了,人们的胳膊从公共汽车开启的窗户中伸出,就像鱼鳍一样。太阳崇拜者在旅馆房顶和水边长椅上晒太阳,建筑钢筋工穿着T恤、背心,或者干脆光着膀子,在高空钢梁上走动。
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上挤满了不想赶路的人们。他们专挑阴凉地儿走,有时还会在公园湖中懒洋洋地戏水。一些人试图叫醒中央公园里的海狮,让它们跳入凉水中,但海狮根本不理睬他们。从曼哈顿出租公寓的窗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胳膊上满是脂肪的女人,手托着下巴,正在观看下面运动的人群。在格林威治村,玩滚球游戏的人们节奏都放慢了。商人们在大声宣传速干女衣及免熨套装的好处。在附近的商店里,人们常用“天儿真热啊!”这样的话来评论酷热的天气。
“天儿真热啊!”
“还用说!”
“天儿真热啊!”
“没错儿!”
“天儿真热啊!”
“他妈的!”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没错儿!”
在纽约,这样的天气没完没了,一直持续着。人们相互之间只有这句话。纽约,正像作家汉密尔顿·巴索所讲,是一座到处是邻居却感觉不到邻里之情的城市。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
如果能发生某件不寻常的事——那么地铁中的那个男孩就能和那个女孩讲话了……
如果人们能自己查电话号码,那么电话接线员就可以多抽一口烟,多歇一会儿气……
如果……
1959年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49分,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确实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停电。许多街区都变成漆黑一团,时钟停止走动,啤酒无法冰镇,黄油融化,电视关闭,人们坐在沙龙里在烛光下亲密交谈。简直妙极了!人们终于有别的话题可以谈论了。
很难想象人们在静悄悄地喝酒,或走过想象中的红绿灯的那种感觉。那些被电梯宠坏的房客,不得不步行上楼。人们在黑暗中洗澡然后擦干。男人们还在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刮胡子。
只有那些盲人无所畏惧。下午3点10分,百老汇1880号纽约犹太人盲人协会漆黑的四层大楼内,200个对这个地方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的盲人工作者,带领着70位视力正常的人走出楼梯,把他们安全护送到楼外的百老汇大街上。
等到第二天,灯又照常亮了起来。在这座人们时常谈论天气的大城市里,盲人们被再次遗忘了。纽约各个街区又恢复到以往的状态,直到某个别的事情发生——再一次大楼停电,一场大火,或一件谋杀案。谋杀!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谋杀案更震动周围街区的了,尽管这种震动只会持续几小时。
1959年8月1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一早晨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家城市报纸的助理编辑喝完第二杯咖啡,正在挖空心思地想如何用自己的想象力给老板留下印象。他翻阅桌上的新闻稿件,突然被一则电报吸引,上面写道:“子弹!由于东百老汇207号一家小餐馆和蔼可亲的65岁老板菲利浦·席科勒尔遭抢劫谋杀,纽约下东城的居民们今天已武装起来。警察说……”
这位助理编辑迅速派一位记者去东百老汇207号,交代他要详细地描述一下那个街区的情况。记者到达现场时,看到几十位邻居表情严肃地围在餐馆前,听一位矮小壮实的妇女说话:“为什么要杀人?他都给钱了,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她和其他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抢劫并杀死好心的席科勒尔先生。这位妇女讲,这本是一个安静的社区,清洗的衣物依然可以挂在外面的消防出口处,旧衣服仍然只卖2.5美元。这里仍是吃硬面包圈[9],男人两腮留须的传统犹太社区,但这种传统现在正面临挑战。
房屋开发项目正在取代人们熟悉的出租公寓,波多黎各人正在不断涌入。这些变化带来了种种冲突,偶尔会达到让人去抢劫和杀人的地步。今年8月10日就发生了一名叫席科勒尔的餐馆老板被杀事件。席科勒尔过去一杯咖啡只卖五美分,还把面包施舍给那些付不起钱的穷人。
带着刺眼的闪光灯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众多的电视摄像师和记者洪水般地涌到了这个街区。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道。
“您认为是什么人干的?”
邻居们不愿回答陌生人提出的问题,只是摇头。记者和摄像师们冲到餐馆楼上的公寓里,见到席科勒尔的家人;他们在哭泣,咒骂,并让记者们走开。
“您能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格林先生?”
电视摄像师和记者们都想安慰死者的家属。他们说话时轻声细语,彬彬有礼,因为如果不这样,死者的亲人是不会讲话的,那样记者就会错过头版的消息,同时也就没有广告中间插播的11点新闻中的现场录音了。
但是他们从死者亲友那儿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他们又跑到了大街上,录下犹太裔美国人的低语:“他们非得杀死他吗?”
“菲力浦·席科勒尔可是个好人啊!”
“问题是,谁将是下一个。”
“这么可怕的街区——我们得搬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库蒲先生?”
“发生了什么事,罗林布鲁姆小姐?”
罗林布鲁姆小姐说:“六年前波多黎各人开始涌入。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街区的变化,是在政治家竞选的宣传车驶过之后。车上的大喇叭里广播的已不再是意第绪语,而是西班牙语,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