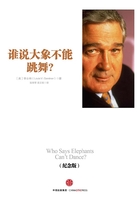
第一章
IBM情缘
1992年12月14日,我刚从一个慈善晚宴上回来,这些晚宴大多充满温情善意,但却少有刺激和促进作用。参加这样的晚宴是纽约城CEO生活的一部分,我作为RJR纳贝斯克公司的CEO当然也不能例外。当我刚走进自己位于第5大道的公寓还不到5分钟,电话铃就响了。那是楼下服务员打来的,现在已经将近晚上10点,服务员却告诉我说:“伯克先生想在今天晚上尽快见到你。”
我很纳闷,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左邻右舍是不会这么晚给自己邻居打电话的。于是我问服务员,是哪位伯克先生,他现在在哪里,以及他是否希望非得在今晚见面?
服务员答道:“是吉姆·伯克,他就住在这幢公寓的楼上,他的确非常想在今晚与你面谈。”
我并不十分了解吉姆·伯克,但我却对他在强生公司的领导才能敬佩不已,例如在处理无麻醉品美国之友(Partnership for A Drug-free America,简称PDFA)的案例上他就表现得非常成功。早些年,伯克还因为处理泰诺污染危机而成为商界传奇人物。我不知道他为何这么急切地要见我,当我给他回电话时,他立刻就下楼来了。
一见到我,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我听说你有可能要回美国运通公司去做CEO,但我不希望你那样做,因为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更大的挑战。”关于我打算重返我曾经工作过10年的美国运通公司的说法,很有可能是他听到了什么谣传。实际上,1992年11月中旬,美国运通公司董事会的3位成员曾在纽约城的“天空”俱乐部与我进行了秘密会晤,在会晤中他们邀请我重返运通公司。运通公司董事会是否给当时的CEO吉姆·罗宾逊施加了压力迫使他下台还很难说,如果是真的,我也会很惊讶,但是华尔街和媒体却一直在流传这样的猜测。然而,我还是礼貌地告诉与我会晤的那3位董事,我没有兴趣重返美国运通公司。虽然我很留恋在那里任职的岁月,但我不打算再回去修正那些在我看来很难避免的错误(罗宾逊两个月后离开了运通公司)。
我告诉伯克这些真相。他立刻对我说,IBM的一个高级职位很快就会空缺,希望我考虑一下是否愿意去填补这个空缺。不用说,我感到十分惊讶。尽管众所周知,而且媒体也广为报道了IBM公司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但还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马上就要更换CEO。于是我说,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IBM的管理工作,因为我没有相应的技术背景。他说:“我很高兴你不打算重返美国运通公司,但是请你再考虑一下到IBM任职的事。”那天的谈话就进行到这里。
随后的几周里,媒体却炒作得很厉害。《商业周刊》刊载了一则题为《IBM董事会将清理门户》的报道,《财富》杂志也刊载了一则报道——《国王约翰(董事长兼CEO约翰·埃克斯)戴着一顶不好戴的王冠》。似乎所有的人都对IBM该如何运作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在阅读这些报道的时候,我也很庆幸自己不在该公司任职,因为媒体至少表面上认为IBM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搜猎
1993年1月26日,IBM宣布公司董事长兼CEO约翰·埃克斯已决定退休,同时公司成立一个搜猎委员会,以便在公司内外考察合适的CEO候选人。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吉姆·伯克,不久他又给我打电话了。
1993年1月,我给伯克的答复和1992年12月的答复是相同的:我不合格,而且我也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强调说:“再考虑一下吧!”
于是,他和委员会在美国展开了一场公开的高级CEO搜猎行动。诸如通用电气公司(GE)的杰克·韦尔奇、联合信号公司(Allied Signal)的拉里·博斯迪、摩托罗拉公司的乔治·费希尔以及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都在他们的搜猎名单中。当然,搜猎名单中也包括IBM公司内部的高级经理。搜猎委员会还与许多技术公司的首脑人物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大约是在就谁才应该坐他们公司的头把交椅这件事征求意见(太阳微系统公司CEO斯科特·麦克尼利公开对一个记者说,IBM应该聘用“一个差劲的人”才是)。在这场被认为是一项头号交易的搜猎行动中,委员会聘用了两家招聘公司,其中重要的负责人是内华达斯宾塞·斯图尔特管理咨询公司(Spencer Stuart Management Consultants N. V.)的汤姆·内夫和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Heidrick & Struggles)的格里·罗奇。
那年2月,我还遇见了伯克和委员会的同事汤姆·墨菲——墨菲当时是大都会ABC公司的CEO。尽管干劲十足,但他们还是没能找到一个技术专家型的,但又具有广泛基础并能给公司带来变化的领导人。事实上,伯克在整个搜猎过程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在搜猎委员会刚成立时就说过的:“我和委员会成员在新的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从哪里来的等方面,都是没有偏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经实践证明有能力的领导人——一个通才和能驾驭变革的人。”
在2月的这次会晤中,我再次告诉伯克和墨菲,我真的不认为自己是IBM一个合格的CEO人选,而且我也的确不希望再掺和到这场CEO搜猎过程中去了。
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再次友好地结束了。当他们离去以后,我猜他们一定还要继续广泛地搜猎,当然也会有同时出现好几个候选人的情况。
专家不得不说的话
我阅读过报纸杂志上华尔街以及硅谷电脑预言家和专家们在那一时期对IBM所做的评论。所有这些评论都加重了我对该公司的怀疑,而且我相信其他许多候选人大概也和我的想法差不多。
在这些评论家中,最突出的大概要数当时几乎在所有媒体上都频频露面的两个人——查尔斯·莫里斯和查尔斯·弗格森。他们写了一本书,叫作《电脑大战》(Computer Wars),该书对IBM的未来持一种悲观的论调。在书中他们写道:“IBM几乎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成为工业界的一支生力军了。比尔·盖茨,这个让工业界所有人既爱又恨且拒绝接受的软件业巨头,也曾经在一个不设防的时刻说过,IBM‘将在几年之内倒闭’。盖茨的话或许是对的。自从1980年以来,IBM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几乎在所有电脑技术领域都落后的失败者……传统的大型电脑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失,但它们却已经是过时的技术了,而且它们曾经在其中引领时尚的王国也已经萎缩。”
莫里斯和弗格森在书中得出结论:“目前的问题是,IBM是否还能够生存下去。而从以上这些分析中显然可以看出,其生存前景的确堪忧。”
莫里斯和弗格森还撰写了一篇更长也更为技术性的,甚至是更为悲观的关于IBM公司的报道,还把该报道以每份几千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些公司和研究所。这篇报道着实让那些贷款给IBM公司的几家商业银行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而且担惊受怕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银行。
IBM的独家新闻报道者、《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保罗·卡罗尔那年也出版了一本书,以记事的形式叙述了IBM的衰落。在该书中,卡罗尔说:“在IBM重振旗鼓(如果还能够重振旗鼓的话)之前,其局面看来相当艰难,IBM将再也不能引领电脑行业了。”
即便是《经济学家》(Economist)这本谨慎且可信赖的杂志也在连续6周里发表了与IBM有关的三个主要报道和一段长篇的编者按。“萦绕在该公司周围的还有两个问题,”编者按写道,“在一个以迅疾的科技变革为推动力,并不断涌现出小型和微型公司的行业中,一家像IBM这样规模的公司尽管组织完善,但是能够迅速应变竞争环境吗?还有,IBM能从急剧下滑的电脑主机市场(IBM正是依靠这一市场赚取了大量利润)上转型,从诸如电脑服务和软件等这些扩张中的市场份额中赚取利润吗?”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或许都是:不可能。”
一向以审慎著称的《经济学家》也指出:“IBM的失败已被视为对美国的一次打击。”
决策
1993年2月总统日那一周的周末,我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当时我住在佛罗里达的家中,喜欢在附近的海滩上一边散步一边整理我的思绪。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疗法。那个周末,我和平常一样进行着每天饭后一小时的散步,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改变了对IBM的看法。促使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RJR纳贝斯克公司所发生的变化。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指出的,KKR显然已经放弃实施计划中的杠杆收购活动,原因有二:首先,正如布赖恩·伯勒斯和约翰·希亚利尔在《大收购》(Barbarians at the Gate)一书中所讨论的,在1988年疯狂的拍卖活动中,KKR以过高的价格购买了RJR纳贝斯克公司。这意味着,KKR除了无力实现所有杠杆收购计划中的重建项目,甚至没有充足的经营杠杆以带来预期的回报。其次,根据菲利浦·莫里斯的说法,来自烟草行业的营业收入也因为RJR纳贝斯克杠杆收购后不久所造成的价格战而备受压力。在这里,菲利浦·莫里斯只不过是在按照麦当劳公司创始人雷·克罗克的建议行事——克罗克曾经说过:“当你看见自己的竞争对手快要淹死的时候,应该赶快抓起消防水龙头并放到他嘴里。”
KKR显然是在采取临阵脱逃战略。正如那天我在海滩上散步时思考的那样,我决定我也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因此,正是我不愿意在RJR纳贝斯克再继续待下去的想法,促使我更多地考虑去IBM公司。
我给多年的好友弗农·乔丹打了电话,在电话里我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乔丹是一名华盛顿律师,也是RJR纳贝斯克公司的一位董事。他证实了我对KKR的感觉,即KKR果然打算取消收购RJR纳贝斯克公司的计划,而且公司的混乱状况也将结束。另外,显然吉姆·伯克也已经与乔丹讨论过有关想让我去IBM的事,因为乔丹知道我是IBM的CEO候选人之一。和往常一样,乔丹的建议总是一语中的,他说:“IBM才是锻造你的地方,因为你是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所以大胆去吧!”
促使我思想转变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总是习惯于接受挑战。IBM的那个职位是一个令人羡慕,甚至有点让人害怕的职位,但同时也是一个吸引人的职位。1989年,我加盟RJR纳贝斯克公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所以从2月15日起,我就在考虑准备接受IBM提供的那个职位以及相关的问题了。乔丹逐渐向伯克透露了我的这些想法,同时我也开始准备向伯克以及委员会提出一些我所关心的问题和顾虑。
过了几天,伯克就给我打电话了,我说我希望考察一下IBM的那个职位,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公司短期和中期规划方面的信息。同时媒体以及专家对该公司的悲观态度让我十分担忧,因为我曾从RJR纳贝斯克公司汲取了一个血的教训,那就是:一家面临着太多挑战的公司,肯定离破产不远了。
我告诉伯克,我想与保罗·里佐会晤。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罗一直是IBM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他已经于1987年退休了,但又于1992年11月被IBM公司董事会返聘回来协助约翰·埃克斯扭转公司的颓势。所以我希望伯克安排我和保罗一起仔细看看公司的预算以及1993年和1994年的规划。
伯克很快就做出了回应。2月24日,我参加在华盛顿特区帕克海厄特酒店举行的一次商务会议时,腾出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与保罗在我的房间里秘密会面。保罗给我带来了公司现有的财政和预算资料。我们之间的讨论是在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中开始的,因为IBM的销售和利润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下滑。更重要的是,现金状况也着实令人担忧。我们仔细查看了每一条生产线以及很多很难加以评估的信息。保罗还明确指出了公司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电脑主机的年收入已经从1990年的130亿美元下滑到了1993年的不足70亿美元,如果这种态势明年得不到控制,那么一切都完了。他还证实,媒体关于IBM在寻求将公司拆分成几个独立的运营单位的报道,也是确有其事。我感谢保罗的诚实和洞察力以及对我的信任,敢于将所有信息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当他离开时,我曾经确信,我绝对不再愿意去IBM公司了。因为根据这些信息资料,IBM获救的可能性不超过20%。一般来说,消费品公司往往会有一些有长久生命力的品牌。但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科技公司来说,显然不是如此。在这个时代和这个行业中,一个产品从诞生、兴起、大获成功,到挫败、消失乃至被人们遗忘,所有过程都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完成。当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已经认为IBM与我的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了。这家公司正在迅速下滑,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有人——任何人,能够及时地扭转该公司的颓势。
但是,伯克并未就此罢休,他这种坚持不懈的姿态或许更多的是由于他越来越发现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担此重任,而不是因为他格外认为我就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在这一点上,我曾经怀疑他只是在力图尽自己的职责罢了。
两周后,我回到了佛罗里达稍事休息,而伯克和墨菲坚持要与我见上最后一面。于是我们选在了一幢新房子里,那是猎头公司的老总格里·罗奇和他妻子在我住的地方附近社区里刚建好的房子,罗奇仅仅是充当了一回主人的角色。在他的新起居室里,只有伯克、墨菲和我3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漫长的下午。
伯克在那天下午做了我所听过的最为新颖的招聘演说:“为了美国,你应该承担这份责任。”他认为,IBM就是美国的财富,因此扭转IBM的颓势应该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的回答是,如果我觉得自己胜任的话,他所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我还是认为这是一项完不成的任务——至少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任务。
伯克继续坚持,他说他正准备请比尔·克林顿总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必须承担这项任务。
汤姆·墨菲,这个在我们先前的会谈中一直让伯克多说话的人,这一次也忍不住对我频频劝说。正如其朋友所指出的,墨菲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人。他强调说,作为一个变革性的企业领导人(这是他的用词),我的经历表明我就是IBM所需要的人。而且他还相信,凭我的能力和正确领导,IBM没有理由不起死回生。墨菲重申了我在伯克以及甚至是保罗·里佐那里所听到的话:IBM并不缺能人和天才,公司所存在的问题本质上也不是什么技术性的问题。
公司的文件柜里塞满了五花八门的制胜战略,可是公司依然毫无起色。此时公司需要的是压得住阵的掌舵领航人下大手笔起死回生。墨菲翻来覆去再三强调,新领导人所要解决的难题恐怕得从战略和文化等层面上推行改革入手,而这正是我在美国运通公司和RJR纳贝斯克十分擅长的。
那个漫长的下午结束时,我已经准备好做出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职业决策,我答应了伯克和墨菲的请求。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已记不清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答应他们的。或许是因为吉姆·伯克的爱国精神,还有汤姆·墨菲的观点,激发了我应对世界级挑战的极大勇气。无论如何,我们握手达成一致并同意起草一揽子财务计划书和公告。
事后想起来也真是有趣,因为无论伯克还是墨菲都认为,将IBM拆分成几个独立的单位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如果他们意识到,公司不仅陷入了财政危机,与客户之间丧失了联系,而且也正高速驶向一个灾难性的后果,那么他们还会这么认为吗?
那个下午我回到家,将我的决定告诉了家人。像往常一样,在这个美满的家庭中,我总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放松。我的一个孩子说:“当然,爸爸,你肯定能办得到!”另一个保守一点的孩子则认为我失去了理智。但是我的妻子,起初是感到十分惊讶,接着就强烈地支持我的决定并为之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