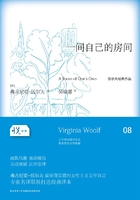
第8章 选篇三(4)
二
现在,要是可以请你们继续听我说的话,场景已经换了地方。落叶依旧纷纷,却已是伦敦,不再是牛桥了。而我必须请你们发挥想象力,设想有这样一间房间,如同其他的千万间一样,往窗外看,越过行人的帽子、一辆辆的货车与轿车,便是对面的窗子。屋内,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只写了几个大字:妇女与小说。遗憾的是,牛桥的午宴和晚餐,似乎让我有了去一趟大英博物馆的必要。唯有把个人的情绪和偶然的几率从这林林总总的印象中一一榨干滤净,才能提炼出纯净的甘露、真理的精油来。因为,牛桥之旅连同那儿的午宴和晚餐,让我心下生出了许多的疑问。何以男人饮酒,而女人喝水?何以一种性别享尽荣华富贵,而另一种却如此寒酸落魄?贫穷之于小说,影响几何?艺术创作,又需要哪些条件?——千般疑问蜂拥而至。但我们需要的是答案,而非问题。而要知道答案,就要去咨询一下博学的先生、公正的大人,他们早就不逞口舌之争、不为身体所惑,而将自己的推理和论断编纂成书、公之于众,陈列在了大英博物馆里。倘若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也找不到真理,我拿起了本子和铅笔,问自己,又要到哪里才找得到呢?
既然准备就绪,既然如此自信,也如此好奇,我就踏上了探寻真理的道路。天虽没下雨,但也阴沉沉的,而博物馆左近的街巷中,那四处可见的地下小煤库,洞口大开,一麻袋一麻袋的煤则在飞泻而下。四轮马车驶来,停在人行道边,卸下一箱箱捆扎结实,兴许是满满一大衣柜的衣物,这一家子大概是瑞士人或意大利人,想在这儿发大财,或是避难,又或许是要在冬天的布卢姆斯伯里[22]旅社里,找到件什么想要的东西。嗓音粗哑的小贩照例推着一车车的蔬菜在街道上熙来攘往。有人大声吆喝,有人唱腔十足。伦敦就像一个大作坊,伦敦就像一架织车。我们都不过是在这台车床上前后穿梭,织出某种图案来。大英博物馆就是这工厂里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几扇转门,我就站到了那恢宏的穹顶之下,就仿佛思想飘进了宽广饱满的前额,一圈响当当的名字[23]让这里熠熠生辉。走到借阅台,拿过一张卡片,打开一卷书目,接着……这儿的五个点,分别代表了我倍感惊愕、迷茫而不知所措的那五分钟。你们知不知道,一年之中,有关妇女的书出了多少本?你们又知不知道,这些书中,有多少是出自男人的手笔?你们可知道,说不定,你们是全宇宙里被人争论最多的生物?我已经备好了纸笔,打算在这儿读上一个上午,满心期待读完之后,可以把真理写在纸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的本领才行,因为众所周知,大象活得久,蜘蛛的眼睛多。另外,我还需要铁爪和钢牙,才凿得开这厚厚的果壳。一页页的卷帙堆积如山,要我怎么才能找得到那么几粒真理的果仁?我扪心自问,绝望之下开始上下打量那长长的书单。即使只有这些书目也值得我去做一番思量。性别与其本质,或许足以吸引医生和生物学家。但令人吃惊、又不得其解的是,性别,其实就是女性,竟然也吸引了令人愉快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那些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什么学位也没拿到的男人,除了不是女人外,看不出有什么资质的男人。这些书里,有几本,一看便让人觉得浅薄可笑。不过,也有很多书,态度严肃、颇有先见,寓意深远而又语多劝勉。只是读读书名,便可想而知,曾有多少男教师和男教士,登上他们的讲台或是讲坛,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就此话题做过长篇大论,以至于通常给予这一话题的时间远远不足以让他们一展才思。这就是最让人觉得奇怪的地方,而很显然——说到这儿,我查阅了字母M那一栏下的内容——这一栏中书的内容只限于男性。女人不写有关男人的书——这不仅让我心下宽慰,因为若是要我先把所有男人写女人的书读上一遍,再将女人写男人的书也通读殆尽,那百年方开的龙舌兰大概都要开上两回,我才能开始动笔行文了。所以,我随便选了那么十来本书,便将我的借阅卡放在了铁丝托盘里,坐回我的座位,与一同来寻找真理精油的人一起等待。
我一边思考究竟为何才有了如此让人好奇的差异,一边在一张纸上画起了车轮,这张纸本是英国的纳税人拿来用作他途的。为何男人对女人的兴趣远大于女人对男人的,至少从这份书单上看是这样的,这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而我也开始浮想联翩,开始在脑海中勾勒,那些在书中谈论女人的男人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年事已高,还是青春年少,已婚还是未婚,有没有酒糟鼻子,驼没驼背——不管怎样,如此为人瞩目,他们不觉间也有些沾沾自喜,只要他们不全是瘸着腿或是老弱病残——我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直到一大堆书倾倒在了我面前的桌上。麻烦现在才开始。牛桥的学生想必受过训练、会做研究,自然有办法绕开弯路,将问题径直引向答案的所在,就像羊儿直奔羊圈一样。就像我身旁的这位学生,正埋头抄录着一本科学手册,我敢肯定,每过十来分钟,他便能从中淘出些真金来。他那满意的咕哝声,无疑就是明证。但若是不幸没在大学里受过这样的训练,那问题大概就不再似羊儿归圈,而是成了惊惶的羊群,在一大群猎犬的追逐下,一哄而乱,四散而逃。教授、男教师、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散文家、新闻记者,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外,看不出有什么资质的男人,全都一拥而上,不放过我那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女人为何贫穷?——直到这个问题变成了五十个问题,直到这五十个问题跃入了湍急的溪流,被冲向不知何方去了。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有我匆匆写下的笔记。为了将我的所思所想公之于众,我会把其中一些读给你们听,这一页上用大写字母简简单单写着这样的标题:妇女与贫穷,不过,标题下面写着的是这样一张单子:
中世纪妇女的状况
斐济群岛妇女的习俗
妇女被尊崇为女神
妇女的道德意识较男人更为薄弱
妇女之理想主义
妇女更为勤恳
南太平洋诸岛妇女青春期的年龄
女性之魅力
妇女被作为祭品而奉献
妇女的脑容量小
妇女更为隐蔽的潜意识
妇女的体毛更少
妇女在心智、道德和体格上较男人更低下
妇女对儿童之爱
妇女更长寿
妇女的肌肉有欠发达
妇女的情感力量
妇女之虚荣
妇女之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之妇女观
伯肯赫德勋爵[24]之妇女观
英奇教长[25]之妇女观
拉布吕耶尔[26]之妇女观
约翰生博士之妇女观
奥斯卡·布朗[27]宁先生之妇女观……
读到这儿,我歇了口气,对,我是在空白的地方又添上了一笔: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28]会说,“聪明的男人从来不会说出他们对女人的看法”?显然,聪明的男人什么也不说。不过,我一边想,一边向后靠在椅子上,抬头仰望着这恢宏的穹顶,飘然而入的思想依然形单影只,而且现在还添上了些许烦恼,这么不凑巧,聪明的男人谈到女人,观点却大相径庭。蒲柏说:
女人大都没有个性。
而拉布吕耶尔却说:
女人爱走极端,跟男人比,不是更好,便是更坏。
他们两个,既是同代人,又都目光敏锐,得出的结论却是针锋相对的。妇女是否有资格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不够格。约翰生博士的意见正相反。[29]她们有灵魂,还是没有?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另一些人则正相反,还认为女人的一半是神,因此对她们顶礼膜拜。[30]有些哲人认为她们头脑浅薄,另一些则认为她们的思想深邃。歌德称颂她们,墨索里尼则瞧不起她们。但凡读到男人谈及女人之处,他们的议论都莫衷一是。我以为,要从中理出头绪来,是不可能的了,同时,我不无妒忌地看了一眼隔壁的那位读者,他的笔记工整,按着一二三的顺序依次排下,而我自己的笔记本上,左一句右一句,潦草凌乱记下的全是些相互矛盾的言论。这真让人沮丧、心烦意乱,我脸上也觉得无光起来。真理已经从我的指缝间溜走了,一滴不剩。
我还不能就这么回家,我想了想,煞有介事地添上一笔,让妇女与小说这项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妇女较之男人,身上体毛稀少,或是南太平洋诸岛上,女人的青春期从九岁开始——还是九十岁?——我的笔迹益发潦草难辨了。忙了整整一个早上,要是拿不出什么更有分量、让人钦佩的东西出来,真是丢人。何况,若是从前我就不能抓住有关W(为了简洁起见,我用此来称呼女性)的真相,那今后又有什么必要再去为W而操心呢?看来,再去向那些学有所专的绅士们求教也不过是白白浪费时间,虽然他们为数众多,博学广识,个个深谙妇女和她们带给政治、孩子、工资或道德的影响,我还不如不曾将他们的书翻开。
不过,就在我沉思的时候,无意中在那原本应该就像我的邻桌一样写下结论的地方,无精打采、毫无希望地画了一幅画。我一直在画一张脸,一幅肖像。这是那位忙着撰写他的传世之作《论女人心灵、道德及体能之低劣》的冯·X教授的脸孔,他的肖像。我笔下的他对妇女而言可是全无魅力。他身材魁梧,下颌硕大,红彤彤的脸上却长着一双极小的眼睛。脸上的表情,一目了然,他在奋笔疾书时准是情绪激昂,下笔有如投枪,一笔一笔落在纸上,犹如捕杀害虫,可惜即使杀掉了害虫,也未能让他如愿,他一定要能继续屠戮才行。即便是这样,也还有让他怒气冲冲、心烦气躁的理由。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我一边问,一边看着自己的画。她是不是爱上了一位骑兵军官?这位军官是不是玉树临风、风度翩翩,身穿一袭翻毛皮装?要么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不是他在摇篮里就被某个漂亮姑娘嘲笑过?因为,我想,恐怕在摇篮里,教授的尊容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不管为何,总之是惹得这位著书立说,大谈特谈女人的心灵、道德和体能如何低劣的教授在我的勾勒下变得怒气冲冲、丑陋不堪。如此画上几笔画,也算是一种休闲的方式,来为一早上的碌碌无为画上个句号。但常常正是在我们的闲暇、我们的美梦中,真理才从藏身之处显露出来。稍稍运用一下心理学的知识——根本不必拿精神分析的名号以壮声威——看上一眼自己的笔记本,我就明白,这幅怒容满面的教授是在怒气中画就的。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愤怒夺去了我的画笔。可我的愤怒又从何而来呢?好奇、困惑、欢愉、厌倦——种种情绪在这个早晨接踵而至,每一样我都可以道出原委。而愤怒这条黑蛇,是不是一直都潜藏其间?没错,这幅素描如是说,愤怒的确潜藏在这诸多情绪之中。毫无疑问,就是那本书、那句话,唤醒了我心中的这条恶魔,就是那位教授的那句女人心灵、道德和体能低劣,我便血脉贲张,面颊滚烫,不禁怒火中烧。这倒没有什么稀奇的,尽管这么做是有点傻。可谁也不喜欢被别人说成天生就比某个小男人还要低劣——我看了一眼身旁的那个男学生——他喘着粗气,打着系好的领带,看上去两个星期都没刮胡子了。人人都有些愚蠢的虚荣心。这只是人之天性,我一边想着,一边画起了车轮,一圈圈绕着教授的那副怒容,直到教授的那张脸看上去就像是烧着了的灌木丛,或是一颗熊熊燃烧的彗星——不管怎样,那已经不成人样、没有人类特征了。这位教授现在不过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31]上烧着了的一把柴火。不一会儿我自己的怒火就得以释怀、烟消云散了,不过好奇还在。那些教授们的怒容该做何解释呢?他们是因何而怒呢?要知道,对这些书留给人的印象稍作分析,便总能觉察到书中涌动着的一股热流。这种热流的表现纷繁多样,或讽刺,或伤感,或好奇,或斥责。而另有一种情绪也常常出现,只是难以立刻看得分明。我称其为愤怒。不过,这愤怒是在暗中涌动,掺杂进其他各种情绪之中的。从它那不同寻常的影响来看,这是遮遮掩掩、错综复杂的怒火,而非简单、直白的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