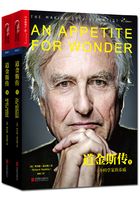
04 温巴山的“金鹰”
1947—1949年,我在温巴山中的金鹰学校读书。跟每一位离家的7岁孩子一样,我也想念妈妈,并把具有母性关爱的女老师想象成母亲。在金鹰,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儿童间毫无限度的残忍,同学们纠集在一起欺负某个同学的情景,让我印象深刻。
金鹰学校,曾经是掩映于高高的温巴山脉那茂密的针叶林中的一所全新的寄宿学校,位于津巴布韦(当时称南罗得西亚)的莫桑比克边境附近。之所以说“曾经”,是因为学校已经因为这个不幸国家后来发生的冲突,而永久地关闭了。金鹰学校的创始人是弗兰克·“坦克”·凯利(Frank“Tank”Cary),他曾任牛津龙校(Dragon School in Oxford)的舍监。在我看来,龙校是全英格兰最大、最优秀的预备学校,充满美好的冒险精神,也拥有许多知名校友。“坦克”来到非洲寻找新的机会,他成立的金鹰学校,忠实地传承了龙校的优良品质。我们有相同的校训(面朝太阳——“Arduus ad solem”,格言出自维吉尔的叙事诗),有相同的校歌,校歌的曲调与苏利文(Sullivan)的《基督教士兵前进》(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相同。“坦克”在马拉维招募学生的时候,曾拜访过我们位于利隆圭的家。我父母很欣赏他,认为金鹰学校很适合我。格林医生和格林夫人也为戴维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于是,我俩一同去了金鹰学校上学。
我对金鹰学校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似乎只在那里读过两个学期,而学校刚刚成立后的第二个学期,我就到那里上学了。我记得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当时被称为“开启日”。这种说法,总是让人想起赞美诗《上帝在很久以前的帮助》中提到的开启日:
时光如同荡漾的河流,
夺走所有的子孙;
他们像梦一般飞翔、被遗忘,
于开启日离去。
赞美诗
在金鹰学校,赞美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全力打响正义之战》这样的赞美诗,都能唱出无比乏味、昏昏欲睡的音调,与其说是打仗,不如说是催眠更恰当。学校要求所有家长为孩子带上一部《圣经》。而我的父母,出于某些原因,只给了我一本《儿童圣经》。这本《儿童圣经》与原版相去甚远,令我有种被忽视的感觉,和其他孩子有些“不一样”。《儿童圣经》没有分章节,在我看来,这样的简化实在不可取。我非常欣赏《圣经》中将章节细分以便查找的方法,为此,还参照同样的方法,为我的一些故事书编上了章节和段落。最近,我偶然看到一本《摩门经》(Book of Mormon),这本书是19世纪一个名叫史密斯的江湖骗子编纂的。我发现,他也对钦定版《圣经》非常痴迷,将他的书也规划出段落章句,模仿出16世纪的英文风格。仅凭这最后一点,就能判定他是个骗子。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想到这一点。难道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认为《圣经》一开始就是以廷代尔和克兰默风格的英文撰写的吗?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如果将带有“事情就这样应验了”的句子全部删除,《摩门经》就会简化成为一本小册子。
在金鹰学校就读期间,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莫过于休·洛夫廷(Hugh Lofting)的《怪医杜立德》(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我是在学校图书馆找到这本书的。现在,因为书中的种族歧视思想,已经严禁登上图书馆的阅览架了。我们可以理解其中的原由。乔利金奇部落的邦珀王子沉溺于童话故事而无法自拔,非常急切地想要成为青蛙后来变成的那位王子,或是灰姑娘爱上的那位王子。因为他面孔黝黑,担心会吓到被他吻醒的睡美人,于是就去求杜立德医生,将他的脸变白。现在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本出版于1920年的平淡无奇、毫无争议的故事书,会在20世纪晚期的时代思潮中犯错误。但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进行道德宣讲,那么我认为,富有想象力的《怪医杜立德》,包括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怪医杜立德之邮局》,都因突出的反物种歧视精神,而弥补了其中星星点点的种族歧视缺憾。
具有母性魅力的“科普斯”
除了校歌和校训之外,金鹰学校还沿袭了龙校称呼老师昵称或受洗名的传统。我们称呼校长为“坦克”,就算是他惩罚我们的时候也不例外。最初,我以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房顶上接水的那种水槽,但现在我意识到,它一定是指残酷无情、不可阻挡的军用车辆。也许,大家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是因为“坦克”在龙校工作的时候,有了顽固不化的名声,无论遇到什么阻碍都坚持走直线,绝不绕道。金鹰学校的其他几位领导,包括克劳德(也是从龙校过来的)、迪克(每周三下午课间休息时,他都会为每人分发一大块巧克力,因此备受欢迎),还有教法语的匈牙利人保罗。沃森夫人为大部分低年级男生上课,被大家称为“沃蒂”,管家科普尔斯通小姐,被称为“科普斯”。
我不敢说我在金鹰学校度过的那段时光是快乐的,和每一位离家独立生活的7岁男孩一样,我也有自己的感触。其中最典型的想法,就是每天清晨当科普斯趁我们熟睡之时做寝室巡查时,我总是幻想着,她会神奇地变成我母亲。我会为此不停地祈祷。科普斯有着与母亲一样的深色卷发,在我天真幼小的心灵中,认为将她的样子变成母亲,应该用不了多大的法术。我还信心满满地认为,其他男生一定会像喜欢科普斯那样喜欢我母亲。
科普斯散发着母性的魅力,和蔼可亲。我倾向于认为,她在第一学期结束时给我写的考评,并不是完全没有流露出喜爱的情感。我记得她是这样写的:“只有三种速度:慢、非常慢、停止不动。”有一次,在科普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说的话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那时的我,不知为什么非常害怕失明,可能是因为有一次看到一个非洲人直直地瞪着只有眼白的双眼,把我吓到了。那时我总是担心,说不定有一天我就会变瞎或变聋。在经过痛苦的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虽然变瞎和变聋都十分恐怖,但最恐怖的还是莫过于变成瞎子。金鹰学校设备十分先进,拥有自己的发电机,平时点电灯。一天晚上,科普斯正与我们在寝室里说话,发电机突然停止运转,电灯随即全部熄灭。我害怕地颤抖着,问道:“是不是灯灭了?”“没有,”科普斯用轻松的语气开玩笑道,“一定是你瞎了。”可怜的科普斯啊,她根本不知道这样一句玩笑话对当年那个小男孩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
我也很怕鬼。在我的脑海中,鬼有着十分具体的形象。它们是眼窝空洞、走起路来“咔嗒咔嗒”响的骷髅骨架,它们以飞快的速度从长长走廊的另一端冲向我,手中举着铁镐。它们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吸,每次都能精准地喷到我的大脚趾。我还有被人煮熟吃掉的诡异幻想。我不知道这些可怕的想象究竟源自哪里。我没有读过这类书,父母也绝对没给我讲过类似的故事。可能是从寝室里其他男生的信口胡说中听来的。这类男生,我在下一所学校中见到了不少。
儿童间毫无限度的残忍
在金鹰学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儿童那毫无限度的残忍。我很幸运,没怎么被人欺负,但同学中有个外号叫“佩吉阿姨”的男孩,却时常被人取笑,而取笑的原因,就是他的外号。正如《苍蝇王》中上演的一幕,他会被许多男生团团围住。这些男生围成一个圈,边跳边单调乏味地唱着“佩吉阿姨,佩吉阿姨,佩吉阿姨”。可怜的男孩总是被欺负得发了狂,盲目地冲向围成圆圈的男生们,挥舞着拳头在空中乱打。一次,我们围观了他一场持久而严重的斗殴,只见他与一个名叫罗杰的男孩在地上打起了滚。我们都十分敬畏罗杰,因为他已经12岁了。围观者都比较同情罗杰,因为他外表英俊、体育成绩优秀,而对受欺负的小男孩无动于衷。这样可耻的事情,在小学生里十分常见。最后,“坦克”校长出面制止了这场斗殴,并于第二天早上训话时提出了严正警告。
每天晚上就寝前,我们都要跪在床上,面朝床头的墙壁,轮流进行晚安祈祷:
上帝,恳求你照亮我们的黑暗;用你伟大的仁慈,保卫我们免于夜晚的危险。阿门。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句话的文字版,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每个晚上,我们都像鹦鹉一样,从彼此处学舌,结果这句话就慢慢地被篡改得毫无意义。如果你对迷因理论感兴趣,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测试案例;如果你不感兴趣,不清楚我在讲什么,没关系,请跳到下一段落。如果我们明白那句祈祷词的意思,就不会随意歪曲和篡改,因为其意义拥有一种“常态化”效果,与DNA“校对”相似。正是这种常态化,使得迷因能够在足够多的“世代”中生存下来,实现与基因的类比。但由于祈祷词中的许多说法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模仿词汇语音学上的发音,结果,随着这些句子和词汇在男生间彼此模仿的“世代”中传递下去,就形成了非常高的“突变率”。我想,针对这一效果展开一场实验,一定会得出十分有趣的结论,但至今尚未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
学校的一位领导,或是“坦克”或是迪克,常常领着我们合唱。合唱的曲目有《开普敦赛马》,还有:
我有六便士,非常可爱的六便士,
供我一生享用的六便士,
两便士用来借贷,两便士用来支出,
还有两便士带回家给老婆。
另外一首歌曲中,老师教我们要发出“鸟儿”的儿话音。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想想,很可能是因为这是一首美国歌曲:
我们坐在这里,像荒野中的鸟儿,
荒野中的鸟儿,
荒野中的鸟儿,
我们坐在这里,像荒野中的鸟儿,
生活在德梅拉拉。
龙校著名的冒险精神,也传到了金鹰学校。记得有一天,校长为全体学生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马塔贝列人和马绍那人”游戏(这是非洲当地版的“牛仔与印第安人”,使用的名字是罗得西亚两大部落的名称)。游戏过程中,需要参与的玩家在温巴山(在当地修纳语中,“温巴”的意思是雾霭之山)的密林和草地上漫游。天知道我们这群小孩是怎么没有跑丢的。虽然学校当时没有游泳池(我离开后修建了一处),但老师们还是领着我们去一处瀑布脚下的美丽池塘中游泳(裸泳)。这是令我们更为兴奋的游戏。既然有天然瀑布,哪个男孩子还会想在人造游泳池里玩水?
我是乘飞机前往金鹰学校的,对一个年仅7岁的男孩来说,独自乘飞机旅行,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探险。我乘坐的飞机,是一架从利隆圭飞往索尔兹伯里(现在的哈拉雷)的双翼飞机,从那里,我还要继续赶路,前往乌姆塔利(现在的穆塔雷)。一位金鹰学校同学的父母生活在索尔兹伯里,本应在那里接应我,送我继续旅行,但他们没有按时出现。我用了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在索尔兹伯里的机场里一个人打转(现在想想,应该没有那么长时间)。陌生人都对我很友善。有人给我买了午饭,还有人让我到机库里转了一圈,看看那里的飞机。奇怪的是,记忆中的那一天是很快乐的,我并没有因为独自一人或被人放了鸽子而感到害怕。最终,同学的父母还是出现了,我成功到达乌姆塔利。“坦克”在机场用他的吉普旅行车“威利斯”接上了我。我很喜欢他的车,因为这部车与我家的“詹妮”很像,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是将记忆中的故事讲述了出来。戴维·格林的记忆与我不同,我想可能是因为有两趟旅行,一趟是我和他两人同行,另一趟是我独自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