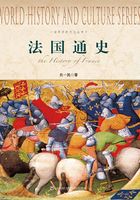
第3章 史前与高卢时期(2)
这一现象立即引起了当地人的担心与不满,当时,恺撒把高卢的居民分为三大部分:1.阿基坦人,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和加隆河之间的地方。2.高卢人,居住在加隆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方。3.比尔及人,居住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方。率先图谋反抗罗马人的是比尔及人。他们通过互派密使,相互串联,试图建立联盟把罗马人赶过阿尔卑斯山去。
恺撒闻悉此事即决定先发制人。他首先向比尔及人发起进攻。继在萨比斯河大败以纳尔维为首的比尔及联军后,他又率军穿过整个高卢直下阿基坦。在征服了阿基坦人之后,他继续挥师北上至布列塔尼半岛,摆平了该半岛上的文内几等邦。
显然,征服进展颇快。这一状况之所以会出现,似乎可归因于高卢自身的四分五裂和政治混乱。当时,高卢在政治上有如一盘散沙。“同族的亲情、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竟阻止不了他们反目成仇”。正是这种深刻的分裂状态,使高卢成了恺撒唾手可得的猎物。因为他可以通过煽动不和和制造分裂,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征服进展的神速并不能掩盖克尔特人传统的好战精神。事实上,就连恺撒本人也在其《高卢战记》中对此大加恭维。他写到:“这是一个极其灵巧的种族,他们有非凡的本领来模仿他们看见别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挖掘坑道,使我们的土方工程倒塌。由于他们有大铁矿,熟悉并使用各种地道,他们的这种技艺更为出色。他们的城墙都设有望楼,望楼由走道相连,并用兽皮防护他们阻挠我们的坑道峻工,向还没有遮盖的坑道抛射削得尖尖的,并用火烤硬了的木块,滚烫的树脂,巨大的石头,以此来阻止我们把坑道挖到城墙脚下。”不过,恺撒对这种好战精神的大加赞赏,其主要用意则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这位高卢的征服者显得更了不起。
四、高卢的罗马化
对于恺撒征服高卢在法国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法国历史学家历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应属以下两种。一些史家为恺撒的胜利而庆幸,他们认为,这一胜利为法兰西进入拉丁世界奠定了基础,使拉丁文明成为当今法兰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些史家则把恺撒的征服视为“法兰西民族”历史的灾难。他们认为,这一征服导致了“法兰西民族”独特演变的终结,它意味着强盛的“法兰西”的毁灭。他们当中民族主义情绪最为明显的个别史家甚至宣称,没有罗马征服,高卢有可能吸收已在马赛立足的希腊文明。后者的证据之一是,在当时的高卢,使用希腊字母者并非只限于少数文化精英。
诚然,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的论战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尽管高卢人曾对罗马人进行反抗,并在公元前52年在一个年轻、勇敢的民族英雄维金格特里克斯的领导下把这种反抗推向高潮,但被征服的高卢很快就对战胜者屈服,向意大利和地中海的文明敞开了大门。由此,高卢进入了罗马化的时代。
恺撒在完成了征服高卢的大业后,尚未来得及在高卢建立一套完整和有条理的政治行政制度,即在公元前44年因遭共和派的暗杀而一命呜呼。因而,高卢罗马化的进程是在其政治上的继承人屋大维的手中基本完成的。屋大维是恺撒的甥孙,罗马“后三头”之一。公元前27年,屋大维从罗马元老院得到“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含有“神圣”、“庄严”之意。尽管此时的屋大维堪称罗马的第一个皇帝,但他因害怕自己也像恺撒一样被共和派暗杀,因而他尚不敢公开把自己称为皇帝,而是称自己为“第一公民”,意即“元首”,同时,以带有共和制外形的元首制之名行帝政制度之实。
屋大维上台后整顿改革了罗马行省统治制度,把行省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前者由元老院任命的执政官统治,后者则直属屋大维统治。鉴于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高卢的贡税对罗马财政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把高卢分为4个行省,即纳尔榜南锡斯(今法国南部)、阿基坦尼亚(卢瓦尔河以南的法国西部)、鲁格敦南锡斯(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比尔及卡(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延伸到今日的瑞士)。除第一个行省被元老院治理外,其余3个行省皆为元首行省。
罗马在高卢的统治中心当属里昂。这里既是高卢诸省总督的驻地,又是罗马统治者召开高卢人代表大会的场所。这种代表大会是罗马人统治高卢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象征。它每年召开一次,由高卢各部落区推选代表参加。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向奥古斯都圣像和罗马女神像献祭致敬,以表示高卢人对罗马和奥古斯都的忠诚。与此同时,它又是罗马政府的法令、告示和高卢各族人民的请愿、陈情上行下达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恺撒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即颇为注重拉拢、收买高卢的上层人物,那么,屋大维在接手高卢后显然在推行这种怀柔政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赋予他们罗马公民权,让他们充当罗马元老和担任募自高卢的辅助部队的司令官,或省区和城市行政机关的官员。
屋大维及其继任者在政治上对高卢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治的同时,还竭力通过推行拉丁文化同化高卢人。而由于高卢人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更为拉丁文化的传播洞开了方便之门。在罗马化的高卢,拉丁文是官方使用的文字,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是全国的正式语言。当然,拉丁语起先只是被高卢上层人物所接受,到后来才变成一般人民的语言。作为后话,高卢地区的拉丁语经过长期演变成为中世纪的罗曼语,后来又逐渐发展为现代法语。
推行拉丁文化固然是罗马人同化高卢人的重要环节,但同化过程的最后完成却得归因于“罗马的和平”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在当时的经济繁荣景象中,给后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则是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升。新建的城市当然是罗马式的:街道笔直、整齐,呈南北、东西走向。市中心拥有一个宽阔的长方形大广场以及包括政府机关、神庙、竟技场、公共浴室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在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公共建筑周围,则是店铺、作坊和富有者的住宅。当时的城市中充斥着一批富裕的市民。他们有的是身为司法官的阔绰的有产者,有的是飞黄腾达的商人,有的是骑士等级的成员,等等。这些人均为“罗马的和平”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在城市中拥有华丽的住宅,而且大多还在乡间建有富丽堂皇的乡间别墅。如图卢兹附近的蒙莫兰别墅竟有不下150个房间。
虽然城市建设有了迅速发展,但人们仍不能对城市化估计过高。当时,绝大多数高卢人仍居住在乡村。各城市的人口数目普遍不是很大,中小城市是四五千人,波尔多只有2万人,即使是作为中心城市的里昂,此期的人口亦从未超过8万人。
当然,高卢罗马化最重要的标志还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在高卢的确立与发展。先前,高卢并不存在意大利那样的奴隶制大庄园。而今,高卢——罗马贵族的奴隶制大庄园到处建立。奴隶们不仅大批地在高卢——罗马贵族的土地上辛勤耕作,而且还得在矿山和公共工程中拼命干活。更有甚者,一些奴隶还在竞技场上成为贵族们的玩物。应当说,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是相适应的。故而,罗马奴隶制经济曾经长期繁荣。而已作为罗马奴隶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卢奴隶制经济也同样呈现出繁荣景象。
五、罗马帝国晚期的高卢
随着高卢罗马化进程的步步深入,高卢的命运与罗马帝国本身的兴衰已然紧密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谓是一兴俱兴,一衰俱衰。直至公元2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依然繁荣昌盛,因而,高卢也照旧安享“罗马的太平盛世”。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晚期,确切地说在公元170至180前后,罗马帝国的统治开始不稳,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危机昭然若揭。进入3世纪后,罗马帝国更是深深地陷入“3世纪的危机”。如前所述,晚期罗马帝国的衰亡必然会在高卢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反应至少表明在两个方面。
首先,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危机很快蔓延到高卢,致使高卢手工业衰落,商业行销范围缩小,城市生产枯萎,城市经济凋敝,广泛利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矿山等已无利可图,难以维系,自由农民(包括中小地主)纷纷破产,奴隶与隶农的生活、劳动状况更形恶化。凡此种种,使高卢的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整个高卢犹如一堆干柴,只要落上几点火星,很快就会燃出熊熊烈火。
其次,罗马帝国的衰亡弱化了中央政权对包括高卢在内的各个行省的统治,乃至出现了“三十僭主”的分裂局面。在这一过程中,高卢驻军司令官波斯图姆在公元258年率军脱离罗马,自立为高卢皇帝,并建起包括高卢、日尔曼、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高卢帝国”。初时,罗马皇帝伽里耶努斯因忙于同法兰克人、阿勒曼人和哥特人的联军作战,不得不暂时容忍“高卢帝国”的存在。268年,波斯图姆为土兵所杀,高卢分裂。其后,维克托里努斯和他的母亲相继成为高卢的实际控制者。“高卢帝国”的最后统治者是拥有元老头衔的将领泰特里克。公元273年,这位“高卢帝国”
的末代皇帝为镇压国内起义,不得不向罗马皇帝求援。不久,双方达成一笔交易。罗马皇帝允诺赐给泰特里克大笔财富,并让他出任罗马南意总督,而泰特里克则答应交出军队,并使高卢重新归并罗马帝国。
导致“高卢帝国”皇帝甘愿向罗马皇帝俯首称臣的高卢境内的那场大规模起义叫“巴高达运动”,巴高达意为“战士”。起义爆发于波斯图姆统治末年,起义者乘高卢脱离罗马,高卢的新统治者力量薄弱之机揭竿而起,并建立起以农民为步兵,以牧民为骑兵的军队,驰骋在塞纳河、卢瓦尔河沿岸的广阔地区,夺取庄园,杀死庄园奴隶主,攻陷城市,赶跑豪富贵族。由于巴高达运动声势浩大,自知无力镇压的高卢皇帝只得向罗马皇帝求援,并不惜放弃高卢的独立。在罗马皇帝派大军远征高卢后,巴高达运动曾一度转入低潮。283年,巴高达运动再度崛起。义军推举埃里安、阿曼德两人为皇帝,自铸钱币,管理地方事务。两年后,罗马皇帝再度派大军血腥镇压了起义。之后,巴高达运动沉寂多时。但到4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危机的加深,巴高达运动又重新爆发,并在5世纪初蔓延到高卢全境。巴高达运动的数度兴起,对罗马帝国(包括后来的西罗马帝国)的解体起了加速剂的作用。
不过,使罗马帝国和高卢解体的最后动因似乎得归结于“蛮族”入侵。作为西欧最富庶的地方,高卢从3世纪起吸引着拥挤在莱茵河对岸的新入侵者。从3世纪起,日尔曼人几乎每年都要大举入侵高卢,对这块宝地进行掠夺性的袭击。406—409年,来自莱茵河的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也在高卢大肆劫掠。“蛮族”频繁的入侵使高卢的居民备受蹂躏,其中城市蒙受的灾难尤其深重。诚然,后人要对“蛮族”入侵造成高卢人口锐减和经济崩溃的程度作出确切的估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仍有一位法国史学家在其专著《三世纪可怕年代中的高卢》中指出:“我们敢说入侵使居民人口减少1/4乃至1/3。就某些地区而言,特别是在北部和东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由于饥谨蔓延、疾病肆虐,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非命”,与此同时,“乞丐大军遍布全国”。
作者评曰:
在民族成分的复杂性方面,法兰西民族在欧洲的所有民族中也许称得上是首屈一指。事实上,只有对于人种学完全无知的人,才敢说出“法兰西种族”之类的话。法兰西民族在成分上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兰西空间”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片在今天大体呈六边形的地域处在西欧几条天然道路的交叉点上,就像十字路口一样门户大开。因而,从史前时代开始,“法兰西空间”就已经从几个不同方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来源复杂的民族。例如在史前时期,“法兰西空间”就至少被两群人所穿越:其一来自地中海;其二来自中欧腹地。由于其源流不同,种族各异,加之“法兰西空间”地理、气候条件非同寻常的“多样性”,遂使法兰西民族的成员显现出令外国人颇觉惊奇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问你最典型的法国人是什么模样时,你往往会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