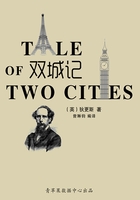
第8章 鞋匠(1)
“日安!”德伐日先生说,低头看着那个低垂着白发的头。那人在做鞋。
那人头抬起了一下,他用有气无力的声音作了回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样。
“日安!”“我看你们这行很累?”
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接着把头抬了起来。那声音回答说,“是——我在工作。”他看着那个人但眼睛里似乎没有光,然后又低下头工作。那声音很小让人觉得可怜,却也很吓人,不是因为体力上的衰弱,虽然关押和低质的食物无疑都起过作用。却是由于长时间的孤独与废弃所导致他身体的衰弱,而这恰恰是他凄惨的特色。他仿佛是漠漠远古的声音那微弱、临近死亡的回响,已完全没有了人类嗓音所具有的生命力与共鸣,就好像是一种曾经美丽的颜色褪败成的模糊可怜的污斑。那声音很低沉,像是从地下发出来的,不禁让人想起在荒野里孤零零地独自走着、疲惫不堪、饥饿待毙的旅人,那无家可归毫无希望的生灵在躺下身子打算死亡的时候苦念着家庭和亲友时所发出的悲伤的声音。
一句话也不说地工作进行了几分钟,他又抬头看了一下。眼里表现出丝毫没有兴趣或好奇,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刚才仅有的那个的客人站立的地方现在还没有空出来。
“我想多放一点光线进来,”德伐日眼睛转也不转地望着鞋匠,“你能够多接受一点么?”
鞋匠放下了他手中的工作,露出一种茫然谛听的神情,望了望他身边的地板和另一面地板,再抬头望着说话的人。
“你说什么?”“你能够多接受一点光线么?”
“你要放进来,我只好勉强承受。”(“只好”两字受到很轻微的强调)。
只是把一线的门开大了一些,临时固定在了那个角度。一大片光线从门缝中射进阁楼,照出鞋匠已停止了工作。一只还没有做完的鞋放在他膝头上。几件非常普通的工具和各种皮件放在脚旁或长凳上。他长了一把白胡子,并不是很长,修剪得很乱。面颊凹陷,眼睛异常明亮。因为面颊干瘦和凹陷,依旧浓黑的眉毛和凌乱的头发似乎显得那双眼睛很大,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天生就大,可现在看去却显得不太自然。他那破烂的黄衬衫领口敞开,露出骨瘦如柴的身子。由于长期没有直接接触阳光和空气,他跟他那浑身破烂的衣衫全都淡成了羊皮纸似的灰黄,混成一片,难以分清了。
他一直用手挡住眼前的光线,那手好像连骨头都透明了。他就一直这样坐着,停止了工作,直勾勾地瞪着眼。在直接注视眼前的人形之前,他总是东张西望,仿佛已忘掉了把声音跟地点联系的习惯。说话之前也是这样,东看看,西看看,又忘掉了说话。
“你今天要把那双鞋做完么?”德伐日问。“你说什么?”“你今天计划做完那双鞋么?”“我也说不清楚,我想是的。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问题使他想起了他的工作,他低下头又忙起活儿来。
罗瑞先生让那姑娘停在门口,自己走上前去。他在德伐日身边站了一两分钟,鞋匠才感觉到他的存在抬起了头。他不是因为看见另一个人而显得惊讶,但他一只抖动的手指却在看到他时放错了地方,落到了嘴唇上(他的嘴唇和指甲都灰白得像铅),然后那手又回到了活儿上,他弯下腰接着工作。那目光和身体的动作都只是一刹那的事。
“你来客人了,”德伐日先生说。“你说什么?”“这儿有个客人。”
鞋匠像刚才一样抬头看了看,双手还在继续工作。“来吧!”德伐日说。“这位先生很了解鞋的好坏。把你做的鞋让他看看。拿好,先生。”罗瑞先生接过鞋。“告诉这位先生这是谁做的,是什么鞋。”好一会儿之后鞋匠才回了话:“我忘了你刚才问的是什么?”“我说,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类鞋,给这位先生介绍一下情况。”“这是一双女鞋,年轻女士走路时喜欢穿的。是流行的款式。我从来没见过那款式。但是我手上有图样。”他带着一丝自豪望了望他的鞋。
“鞋匠叫什么?”德伐日说。现在他的手上再没了工件,他用左手掌捏右手指关节,又用右手掌捏了捏左手指关节,然后用一只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下巴。他一刻不停地依次摸来摸去,每说出一句话他的脑袋里都会一片空白。要想他回想起那段事就好比是维持一个极度衰弱的病人不致休克,或是保持濒于死亡者的生命,希望他能够透露些什么。
“你是在问我的名字吗?”“是的。”
“北塔一0五。”“就是这个?”“北塔一0五。”
他发出了一种既不是赞叹也不是呻吟的厌倦的声音,然后弯腰继续干起活儿来,直做到寂静再度被打破。
“做鞋不是你的职业吧?”罗瑞先生看着他说。他那憔悴的眼睛转向了德伐日,好像是希望把题目交给他来回答,从那儿没得到答案,他又在地下找了一会儿,才又转向提问者。
“做鞋不是我的职业,不是。我——我是才在这儿学做鞋的。我是靠自己独立学习的。我恳求让我——”他又失去了记忆。这一次长达几分钟,这时他那两只手又开始按顺序的寻找了起来。他的眼睛最终又回到刚才离开的那张脸上。一看到那张脸,他吃了一惊,却又平静下来,像是刚刚才醒来的人,又回到了昨夜的题目上。
“我提出请求希望自学做鞋,费了很多力,花了很多时间,终于允许了。从那以后我就做鞋。”
他伸手想要回被拿走的鞋,罗瑞先生依旧看着他的脸,说:
“曼内特先生,你难道一丁点也想不起我了么?”鞋掉到地上,他坐在那儿一直呆呆望着提问题的人。“曼内特先生,”罗瑞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德伐日的手臂上,“你真的一点也想不起这个人了么?看看他,看看我。你心里是不是还记得从前的银行职员,以前的职业和仆人,曼内特先生?”
这位被囚困了多年的人坐在那儿一会儿呆望着罗瑞先生,一会儿呆望着德伐日,他额头正中已被长时期抹去的聪明深沉的智力迹象渐渐穿破覆盖着它的阴霾透了出来,却马上又被遮住了,模糊了,隐没了,不过那种现象的确出现过。可他的这些表情却都在一张年轻漂亮的面孔上真实地得到了反映。那姑娘早已沿着墙根轻轻的走到一个能看见他的地方,此时正注视着他。她最初举起了手,即使不是想把自己与他分开,怕见到他,也是表现出了一种混合着同情的胆怯。现在那手却又伸向了他,发抖着,着急地把他那幽灵样的面孔放到她温暖年轻的胸膛上去,用爱使他复活,使他产生希望——那表情在她那年轻漂亮的脸上重复得那么真实(虽是表现了坚强的性格),竟好像是一道活动的光从他身上转移向了她。
黑暗又覆盖了他,他对两人的注视渐渐地松懈下来,双眼以一种模糊且失意的表情在地上找了一会儿,便又照老样子四处张望,最后发出一声深沉的长长的叹息,接着拿起鞋又干起了活儿。
“你认出他了么,先生?”德伐日先生问。“认出来了,只一会儿。刚开始我还以为彻底没有希望了,可我却在那一刹那毫无疑问地看到了那张我再熟悉不过的面孔。嘘!咱们再离的远一点,嘘!”
那姑娘已离开阁楼的墙壁,走近了老人的长凳。老人正在低头干活儿,走近他的人影差一点就要伸出手来摸摸他,而他却什么都不知道。此中有一种东西令人肃然起敬。
不曾说话,也不曾发出任何声音。她像精灵一样站在他身边,而他却弯着腰在干活。
终于,他要换工具,要取皮匠刀了。那刀就放在他身边——不是她站立的一边。他拿起了刀,弯下腰正要工作,眼睛却瞥见了她的裙子。他抬起头来,看到了她那张年轻漂亮的脸。两个旁观者要走上前来,她却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别动。她并不是害怕他会用刀伤害她,虽然那两人有些不放心。
他略显害怕地望着她,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唇做出了一些说话的动作,虽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他的呼吸急促吃力,时不时地停顿一下,却听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
“这是什么?”姑娘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把双手放到唇边吻了吻,又伸向他。然后紧紧地抱住他,似乎是要把他那衰迈的头放在她的怀抱里。
“你不是看守的女儿吧?”她叹了口气,“不是。”“那么你是谁?”
她对自己的声音不放心,便在他身边长凳上坐了下来。他略微往后一退,但她把手放到了他的手臂上,一阵震颤明显地通过他全身。他平缓地放下了手中的鞋刀,坐在那儿瞪大眼望着她。
她刚才匆匆掠到一边的金色长发此时又垂落到她的脖子上。他缓慢地伸出手来拿起发鬟看着。这个动作才做了一半他又开始犯迷糊了,再次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又做起鞋来。
但他做得时间并不是很长。她放掉他的胳膊,却把手放到了他的肩上。他疑惑地看了那手两三次,好像要肯定它的确放在那儿,然后放下了手上的工作,把手放到自己脖子上,取下一根脏兮兮的绳,绳上有一块卷好的布。他在膝盖上小心地把它打开,里面有少许头发。只不过两三根金色的长发,是很多年前缠在他指头上被扯下来的。
他托起她的头发,认真的观察。“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可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是怎么回事?”
在认真思考的表情回到他额上时,他发现她居然也是同样的表情,便拉她完全转向了亮光,仔细端详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