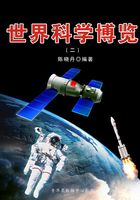
第8章 19世纪的物理科学(7)
当39岁的夫琅和费在1826年6月7日去世时,他留下的遗产不仅有那些精致的透镜,而且还有许多神秘的谱线。后来在1859年,基尔霍夫和本生宣布发明光谱仪,于是有了一系列元素的发现。
一天傍晚,基尔霍夫和本生正在海德堡的实验室工作,这时他们看见十英里远处曼海姆城附近大火燃烧。他们把光谱仪瞄准大火,发现从火焰的谱线排列可以检测到现场有钡和锶的存在,即使相隔这样远的距离。本生开始想到,有没有可能让光谱仪瞄准太阳光,检测太阳有什么元素呢?他咕哝道:“但是人们会以为我们疯了,竟然梦想做这样的事情。”
1861年,基尔霍夫把这一想法付诸实验,从太阳发出的光中,他成功地辨认了九种元素:钠、钙、镁、铁、铬、镍、钡、铜和锌。真是令人惊讶,天空中曾经被古人崇敬为神的巨大光源,竟然含有和地球完全一样的元素。基尔霍夫打开了两门新科学的大门——光谱学和天体物理学,同时在地球上的物理学与化学和统治恒星的物理学与化学之间建立了另一种联系。这是又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曾经被认为是完全分离的各个领域原来是互相联系的。
1864年,一位名叫哈金斯(William Huggins,1824—1910)爵士的业余天文学家,首次把光谱仪对准深空天体。他是一位富人,拥有私人天文台,配有望远镜,它们就位于伦敦的山上。他把光谱仪安装在望远镜上,研究两颗亮得可以用肉眼观察的恒星所发出的谱线,这两颗星是毕宿五(金牛座中的一等星)和参宿四(猎户星座中的一等星)。他能够辨认出铁、钠、钙、镁和铋等元素的指痕印证。然后他又试着观察一个星云,带着悬念和敬畏的心情。他在杂志上写道:“难道我不是在深入观察创世这一神秘之处?”也许此刻他将为不同星云理论的对错给出最终判决。
“我透过光谱仪,没有期望中的光谱,只有一根明亮的谱线!……星云之谜就这样解决了。答案就来自于光线本身,这就是,它不是大量恒星的集合体,而是发光的气体。如果恒星遵从与太阳同样的规律,并且属于更亮的等级,就会给出不同的光谱,但这一星云的光显然来自于一种发光气体。”
遗憾的是,哈金斯一开头就走错了路,由于这颗星云是气体状的,他就假设所有的星云,包括椭圆形状和旋臂形状的星云,都是气体组成的。但是,无论如何,第一次把光谱仪用在天文学上确实是一项惊人的成功。夫琅和费线和光谱仪对天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好比化石对地质学研究的意义,它们为气体星云和恒星的温度、组成以及运动提供了无比珍贵的信息。正如基尔霍夫证明的那样,热的、发光的、不透明的物体会发射连续光谱——彩虹所显现的各种颜色,没有谱线出现。然而,观察一团冷却的气体,在光谱中就会出现吸收暗线。这些暗线揭示了气体的化学成分。但是,如果从一个角度观察气体,看到的会是另一种不同模式。这些工具成了天文学家研究气体星云的罗塞塔石碑。
约翰·赫歇尔是威廉·赫歇尔的儿子,他把他父亲的星表扩展到南半球,库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是把摄影术用于天文学和测量太阳能输出的一位先驱者。给恒星照相
约翰·赫歇尔是威廉·赫歇尔的儿子,他第一个认识到摄影术用于天文学的可能性。[其实,摄影术(photography)就是约翰·赫歇尔造的词。]尽管摄影术发明于1826年,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在天文学中应用。一旦引入了这一新工具,摄影术很快就在天文学中流行起来,虽然如今又有计算机的加盟,但摄影术仍然是天文学的关键工具。当然,它的好处就是天文学家再也无须实时工作,他们可以从照片作出判断,也可以在获得照片后,在任意时间里与照相图片打交道。
他们可以用放大镜或望远镜聚焦在特殊的区域,比较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它们留下的记录之精确,为任何手工操作所不及,无论一个人的视觉有多敏锐。随着摄影术这一媒介变得越来越方便,它可以让底片在很长的时间里曝光,以捕捉那些甚至用望远镜往往也很难看到的对象。1889年,巴纳德第一次拍摄到了银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摄影术成了天文学家越来越重要的工具,现在它已为考察和研究留下了浩瀚的图像数据库。
再次认识太阳
对我们来说,最近也是最重要的恒星当然是太阳,19世纪又有两项发现,使我们增加了对太阳物理学的认识。1843年施瓦伯(Samuel Heinrich Sehwabe,1789—1875)宣布发现太阳黑子的周期性活动。伽利略曾经第一个检测到太阳上有黑子存在,现在施瓦伯认识到它的周期性,这就为太阳的内部机制带来了新的看法。这一发现标志着太阳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早期工作的开始。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成果是在太阳的组成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这种元素在地球上从未被检测到过。1868年詹森(Pierre-Jules-Cesar Janssen,1824—1907)在研究太阳光谱线时第一次发现了氦的存在。
与此同时,开尔文勋爵和亥姆霍兹根据他们对太阳内部发光机制的考虑,认为地球的年龄最多是2000万到2200万年。但是,当时的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认为的地球年龄却是差异极大。开尔文勋爵为了探询地球的确切年龄,还研究了地磁学、水力学、地球的形状和地球年龄的地球物理学测定方法。他很快发现自己正处于地球年龄争议的中心,因为他估计的太阳年龄只有2000万年,不足以为地球上的生物进化提供足够时间,而诸如赫顿和莱伊尔等地质学家对地球历史则有更长的估算。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时采用的是莱伊尔的数值,他假设地球的地质历史跨度至少是3亿年。最近的21世纪对太阳发热机制的认识支持达尔文,而不是开尔文。
测定地球年龄
地球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受的是完全不同的训练。尽管矿工和工程师对我们立足的大地早有研究,但是地质学和天文学不一样,作为一门科学它还只是在18世纪以后才开始发展,直到19世纪才达到全面成熟。
18世纪结束时,地质学家们正在进行一场大争论,研究者各执一词,有的主张水成论,有的主张火成论。水成论的主将是杰出的德国地质学家魏尔纳,他主张地球上所有地层都是原始洪水冲积后的沉积物。火成论的主将是苏格兰地质学家赫顿,他认为地球形成的主要驱动机制是内热,以火山爆发的形式周期性地冲出地壳。
在这两大学派中,火成论更为激进。水成论把地球历史看做就是一次唯一性事件的结果,一场巨大的洪水(类似于《圣经》中的诺亚故事),使地球的地壳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跟《圣经》中创世纪故事的字面含义非常吻合。学者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地球年龄不超过6000年。赫顿以及火成论者则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地球历史经历了漫长、缓慢和持续的变化过程。他们认为,如今在地球表面观察到的各种作用力,它们始终在起作用。形成、磨耗和重塑的过程反复上演。其他一些过程也在持续进行,例如,熔岩穿过地壳喷发,玄武岩和花岗岩之类的结晶岩在持续形成,地表上岩石的沉积层在不断堆积。这一观点被认为是激进的和理性主义的(把推理看成是唯一的权威),因而从一开始就饱受怀疑。
法国伟大的比较解剖学家居维叶就是反对者之一。居维叶提出地球历史中的一系列灾变证据,在灾变期间所有物种都灭绝了,然后,新的岩层形成。他说,最近的一次灾变就是圣经中描述的大洪水。
地质学家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1807—1873)也独立主张灾变论,认为地球经历过一段冰期——实际上,有20次冰期——其证据是:现在不存在冰河的地区却出现了某些冰期才有的现象。尽管冰期理论一开始遭到反对,但当证据越来越多时,已逐渐被人们接受。
179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往往被称为地质学的英雄时期,因为此时的地质学受到来自艺术和哲学中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浪漫主义者拥抱大自然,鼓励探险活动,他们热衷于远离无趣乏味的文明社会,走向未开化的原始荒野。于是,行走于崇山峻岭之中成为时尚,响应这一号召的科学家,投身于变幻无穷的大自然,零距离地面对地壳的形成过程,而在从前他们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仅当此时,地质学才不再只是单纯地研究矿物学,辨认孤立的岩石标本,而是成为一门大有作为的科学,根据地球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剧变、侵蚀及其重造事件——它们是一段惊心动魄的伟大历史,反映了地球上各种力量的彼此较量——来解读地层。
当然,老顽固们还在抵制。这是一些固守传统方法的地质学家,他们关心的只是这门科学的声望、证据的搜集和理论的完整。浪漫主义者经常与这样的传统地质学家发生冲突,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捍卫真理的骑士,准备面对由此产生的后果,献身于对大自然的探险事业。
其实,这两种倾向无须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它们也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双方所用的方法。保守、宗教和反革命的心态正是法国革命之后的时代特征,它迫使地质学严格依附于经验主义,也就是说,寻求具有严密证据的理论支持。其结果是,即使受随心所欲的浪漫主义影响的地质学家,在考察岩层和搜集样品时采用的也是和他们的同事们完全一样的方法。
到了1830年,更多的事实已经呈现,从中足以引出理论,同时赫顿的均变论还引起一位富有的年轻苏格兰律师的关注,他对地质学比对法律更为关注。他就是莱伊尔,尽管他是在牛津大学跟一位水成论者学习地质学的,但他在欧洲到处旅行,有机会亲自考察许多岩层。他在研究中得出结论,赫顿是正确的,形成地球历史的各种作用力在时间的长河中始终如一,即便在当代依然行之有效,表现为侵蚀和沉积、加热和冷却等现象。他还广泛阅读——远远超过赫顿——尽管他本人没有作出什么发现,也没有提出自己的理论,但他的巨大贡献是把许多事实汇集到了一起。
他坚持说,只有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地质因素,才可用于解释过去的历史,当然需要假设经历了非常之长的时间。他写道:
“相比于各种先入之见,大大低估已有时间跨度这一作法更是危害地质学的进步,除非我们使自己习惯于思考这一可能性:曾有一个无限久远的年代……否则我们将不幸形成极为危险的地质学观点。”
1830年,莱伊尔出版了《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其中的一本次年被带上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舰,成为旅途中的阅读佳品。这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