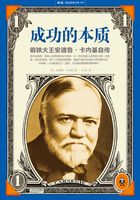
第5章 当起小信差,一周赚2.5美元(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工作。我刚刚满13岁,十分渴望能找到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对前景的展望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噩梦。当时我一直这样想,我们每年一定要赚满300美元,就是每月25美元。这是经过我计算,能够保证我们生活所需,不需要依靠他人的数目。
当时的生活必需品还是相当便宜。
霍根姨父的兄弟常常问我父母准备让我做什么。有一天,我目睹了一件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他满怀好意地对我母亲说,我是一个有希望的小男孩,善于学习,他相信只要我拿着个小篮子,摆点小玩意,在码头沿街叫卖,一定能赚不少钱。我到那时才知道女人被激怒后的反应,我母亲那时正在缝纫,听到后立刻跳了起来,伸出双手在他面前摇晃。
“什么!叫我儿子去做小贩,和这些码头上的粗人混在一起!我宁愿把他扔进阿勒格尼河。你走!”她指着门口大喊道。霍根先生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情的女皇。这一刻她崩溃了,但是她只是流了一点眼泪,抽泣了一小会,就把我和弟弟搂进怀里,告诉我们不要介意她的失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只有我们始终做正确的事情,那就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受人尊重和敬仰的人。”这段话出自海伦·麦格雷戈给奥斯巴尔迪斯通的回信。她在信中威胁要把她的俘虏“剁成尽可能多的肉块,就像格子绒上的格子那么多。”
但是导致我母亲生气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因为小贩这个职业太简单——母亲教导我们懒惰才是可耻的,而是她觉得这个职业或多或少有无业游民的特征,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样还不如去死。没错,我母亲情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和他们一起死,也不愿意让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期的奋斗时,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家更值得骄傲的了。这个家充满强烈的荣誉感,独立性,自尊心。瓦尔特·司各特曾说,在他见过的人中,彭斯有着最特别的眼睛。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就像彭斯所描述的:“即使她的眼睛看的是空地,也会闪耀着荣誉的光芒。”
英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任何低下、卑贱、欺诈、诡诈、粗俗、欺瞒和流言。我的父亲也是天性高尚,受到大家的爱戴,是一个圣人。有这样的父母,汤姆和我毫无疑问地被培养出高尚的人格。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父亲发现必须得放弃手工纺织,进入布莱克斯托克先生的棉纺厂工作。布莱克斯托克先生是一位苏格兰老人,就住在我们住的阿勒格尼市。我父亲也在这个厂里给我找到了份工作,线轴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那里——周薪是1.2美元。这是一段艰难的生活。在冬天,父亲和我不得不摸黑早起吃早饭,到工厂时天都还没亮,而在短暂的午休时间后,一直要工作到天黑。这样的作息时间使我压力很大,而这份工作本身也没什么乐趣。
但是就如乌云边总是有银光,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在为我的全部——即我的家庭分忧。后来我赚过数百万,但这些钱无法带来我第一周赚到钱时的快乐。
此时,我是家庭的好帮手,能够赚钱,不再仅仅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常常听见父亲在唱那首好听的《小船一排排》,我很渴望能实现最后几行歌词:
阿莱卡,乔克,吉纳特早早起床去上学,他们将划着小船,我们想要看日出。
我准备划起自己的小木筏。请注意,阿莱卡、乔克和吉纳特是最早接受教育的孩子。苏格兰是第一个要求所有父母,不论贫富,都要送孩子们上学的国家。苏格兰也是最早建立教区公立学校的国家。
不久后,阿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约翰·海先生需要一个男孩,问我是否愿意去为他工作。我去了,每周能赚2美元。但最初,这份工作甚至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厌恶。我得在线轴厂的地下室操作一台蒸汽机来烧锅炉。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每夜都坐在床边摆弄蒸汽压力表,有时担心蒸汽压力太低,楼上的工人们会抱怨没有足够的动力,有时又会担心蒸汽压力太高,锅炉会爆炸。
但是出于自尊,我没有告诉父母这些。他们有自己的麻烦。我必须像个男子汉一样忍受自己的痛苦。我的希望很高,每天都在盼望会发生一些改变。
我不知道会改变什么,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坚持,一定会有转机。此外,在这些日子,我不会忘记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做,苏格兰人应该怎么做。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永远不该放弃。
一天,机会来了。海先生要开一些账单。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写什么字体,然后给了我一些活。结果令他很满意,他发觉以后找我帮他做账很方便。我也很擅长数字。不久后他就觉得让我离开蒸汽机,做点别的事对他更有利。另外,我相信他也是出于好意,要把我从蒸汽机那解放出来,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也是苏格兰人。这份新工作没那么讨厌,除了有一小点。
我现在的职责是把新生产的线轴放进油桶中。幸运的是,这个工作有单独的车间,而且我是单独一人。但是,不管我下多大的决心,对自己的弱点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始终做不到。即使是想起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无济于事。但如果我不吃早餐或午餐,晚餐时我的胃口会好一点,而且那时被分配的任务也做完了。
一个真正的华莱士或布鲁斯信徒是宁死也不愿放弃的。
比起棉纺厂,我为海先生工作是显着的进步,我也结识了一个对我很友好的雇主。海先生使用的是单式记账法,这点我可以帮他做好。但是我听说所有大公司都是使用复式记账法。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商议了此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和威廉·考利,我们都决定参加冬季的夜校,学习这个更复杂的系统。于是我们四个去了匹兹堡的威廉斯先生那里学习复式记账法。
在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家,得知电报公司的经理戴维·布鲁克斯问我的姨父霍根,是否知道在哪可以找个可靠的男孩当信差。布鲁克斯先生和我姨父都是国际跳棋爱好者。他们就是在玩跳棋时谈到这个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小事能产生意义最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重音可能不仅影响个人的命运,甚至还可能影响整个国家。他是一个把所有事都当成小事的有胆识之人。他常说,如果有谁建议他忽略小事,那么有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才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小事是上帝给予的最好的礼物。
我的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还说他会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我比任何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更渴望自由。母亲同意了,但父亲有点犹豫,他说,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年纪太小,长得也很瘦小。一周2.5美元的报酬显然是想找一个大男孩。我也许得在晚上去村里送信,可能会遇到危险。总的说来,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待在我原来的地方。不久后,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愿意给我个尝试的机会。我相信他是去咨询过海先生的意见了。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机遇,虽然正如他所说,我的离去对他是一种损失。但他仍然建议我去尝试一下,如果我失败了,他还好心地说,他愿意帮我保留原来的职位。
决定之后,我要去河对面的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我的父亲想要和我一起去,最后定的方案是,他陪我到电报公司,地址是第四大街和伍德大街的交叉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预示着好兆头。父亲和我从阿勒格尼走到了匹兹堡,离我们家将近要两英里。到达门口后,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
我坚持要独自上二楼去见这位重要人物,接受我的命运。我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有点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了。一开始,其他孩子会喊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没错,我是苏格兰人,我很自豪。”但是在言谈中,我大部分的苏格兰口音已经改掉,只剩下一点。我觉得如果我能和布鲁克斯先生独处,则可以表现得更加聪明。要是我的苏格兰父亲在场的话,可能会笑话我装腔作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