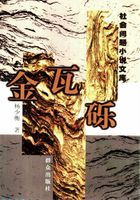
第5章
俞怀颖在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已经干了六年,她在大学里学的是考古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文化局,安排到文管办,六年里这个办公室也就她一个工作人员。俞怀颖对她的工作相当投入,许多人因此觉得她挺奇怪,外行人总认为干此类事情该是些老古董或者老怪物,一个妙龄女子跟这种事有瓜葛令人费解。那些对俞怀颖有所了解的人则认为她简直就是天生干这种事的,这姑娘要不拿着一把小锄到哪个墓坑里刨死人骨头,她还干什么才对?
那天俞怀颖骑着自行车到了三塘村,在村头向村民打听,几经周折找到了村长。这个村的村长是个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听说俞怀颖是市里文管办的干部,咧嘴便笑:“为那破棺材来的?”
俞怀颖挺诧异,说:“村长你听到什么了?”
“不就是修路挖出的那个老墓吗?我知道那个事,那天我就在工地上。”村长说,“里边就是些破板,再就是死人骨头,几乎烂光了,没见什么东西。谁想传来传去传奇了,说有什么金银财宝,陶人彩马的。没那回事。”
俞怀颖扫兴而归。她牵着自行车穿过村子,路过小学校时,校门外边一块黑板引起了她的注意。那黑板上有几行工整的粉笔字,俞怀颖觉得那些字迹很眼熟,她立刻想起给文管办写信的那个“一民众”。
“什么事?”老人问。
俞怀颖注意到这老人有着一头富有光泽的银白色的头发,他微驼,躬着身子,戴老花眼镜,镜框下垂落到鼻尖上,老人的眼光从眼镜镜框的上方向她投了过来。
“请问大门边黑板上的粉笔字是谁写的?”
“怎么啦?”
“字挺好的。”
“也就那样。”老人说,“是我写的。”
俞怀颖挺吃惊。她立刻发问:“您是不是给市里文管办写过一封信?”
“没有。”老人说。
“关于一座古墓的?”
“没有。”老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古墓。”
俞怀颖颇觉失望。她说:“我没事,再见。”
她把自行车推出大门,出门时忍不住回头又看了一眼,她发现白发老人站在操场边,目不转睛盯着她看,老人的眼神非常古怪。
俞怀颖骑着自行车回到市区。一进办公室,劳而无功的三塘之行便被她抛在脑后。
然后过了两天,第三天黄昏下班的时候,俞怀颖推车离开办公楼大门时忽然看到三塘村小学操场上见过的老人。这老人除了微驼的背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头银发,俞怀颖一眼看到他在大门边的人群里,在那一瞬间她吃了一惊,本能地觉得老人出现在这里跟她有关。也许那封信真是他写的,因为某种原因在村里他不敢承认,要上这里找她说明?俞怀颖看见老人还像那天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掉转车头走过去,却见老人身子一闪背过脸,俞怀颖不觉停下来,站在原地看着老人远远走开。
看起来像是偶然碰面。这座城市不算大,生活其间的人偶然相遇的概率不低,只是俞怀颖总觉得有异,在她的感觉里那老人的眼神非常奇怪,不太对劲。
她没想到这位奇怪老人竟然盯住她了。两天以后她去宾馆参加一个文化方面的会议,意外地在宾馆大堂的外边看到有副白头发在人群里一闪而过。又过几天,俞怀颖在自己居住的文化局宿舍楼外再次看到混在人群中的一副异常醒目的银白色的头发。
她明白情况确切无疑,银发老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她身边出没绝非偶然。
那时俞怀颖恰有一个到省城参加短期培训的任务,她整整去了一个星期,回到本市后一到单位上班,她便发现身边气氛有些异常,她的身影从局里几间办公室门口经过时,里边都有人发出哧哧窃笑。
俞怀颖没去找任何人打听。她决定守株待兔,她通常都很沉得住气。
那天下午果然就有一个好事者自动送上门来,那是社会文化科一个主任科员,姓胡,常被戏称“胡主任”。胡主任为中年男性,长着个酒糟鼻子,有打听他人隐私之癖,他在俞怀颖的办公桌前蹭来蹭去,东拉西扯,绕了好大的弯子才进入主题。
“小俞不简单啊。”他说,“你是不鸣则罢,一鸣惊人。”
“我猜那人虽然名不见经传,实际上一准腰裹万贯,民间里真有这种高人。不得了,那真是一往情深。池子里鱼多得很,一家伙钓的就是条大鱼,你小俞厉害。”
俞怀颖问:“这大鱼什么模样?”
“一头的白发。好家伙,银丝万千。”
原来俞怀颖不在的这些天,白发老人居然跑上门在这办公楼上下走来走去。这人挺特别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本大楼负责保安的人发现后把老人叫去盘查了半天,老人除打听俞怀颖去向外,什么都不肯说。由于老人未有出格行径,保安也不敢对他如何,只是驱逐了之,不料老人却不远走,天天在楼外流连,他的头发和脊背过于醒目让人印象深刻,几乎谁都注意到这人的存在,一时间便众说纷纭。俞怀颖很久以来就是文化办公楼里街谈巷议的一个主题,有关谈论的中心是她的性格以及她的孤单。俞怀颖端庄清秀,却总名花无主,三十出头,已逐渐归入大龄女青年准老处女之列,像她这样的人经受众多舌头的多方垂爱在所难免。那些天办公楼里最出奇制胜的猜想是把到本楼来东张西望的神秘老头说成俞怀颖的男友,如今待字闺中的姑娘找一个可以当父亲的老头嫁是一种时髦,通常这种老头要么功成名就要么富甲一方。把擅长挖古墓研究骷髅的俞怀颖跟这种老头扯在一起,泡上唾沫加以咀嚼,无疑津津有味。
俞怀颖没去理会胡主任之流的议论,她感到吃惊的是那个老头,这人如果不是个神经病,他就必然有些缘故。
两天后俞怀颖在机关食堂吃中饭的时候偶然抬头看了窗外一眼,发现窗外有一丛白发在人群中闪耀,俞怀颖把筷子一放便走了出去。
果然是那个老人。俞怀颖径直走到他的面前。
“老人家您吃过饭没有?”俞怀颖问。
老人点了点头。
“我有话要跟您说。”
老人便跟她进了食堂,两人在饭桌边坐下,那张饭桌比较僻静,没有其他人,就他们俩。
“我见过您。”俞怀颖说,“从三塘村小学起,见您好多次了。”
老人没有回答,他把手伸进外衣左侧内的暗袋里,从里边掏出一个旧式铁皮烟盒。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他说。
老人打开铁盒,里边装的却是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照片已经发黄。一个留着长辫,前额略往前倾,眼睛很大的青年女子正从照片上做一种永久的凝视。
老人说:“你看出这是谁吗?”
俞怀颖静静看着照片,她使劲克制着,让自己的手不要发颤。
“这,这,”她问,“谁呢?”
“我猜你一定是田丽琴的女儿。”
“这是她的照片?”
“你怎么会姓俞呢?”
“我妈的照片怎么会在你手中?”
老人垂下眼睑。
“你跟她那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老人道。
俞怀颖不觉浑身战栗。她知道自己正面临一个重大发现,有如她在某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久远的古墓里感觉到的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重大发现却不是关于他人,而是关于她自己。
从懂事的时候起,俞怀颖就时常疑神疑鬼,她总觉得自己不是爸爸的女儿。
俞怀颖是个早慧的女孩,从小多思而敏感。她记得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岁月不断地总颠簸在本城和省城之间的公路上。俞怀颖和父母居住在省城,在本城居住的是她的外祖母一家,从她懂事的时候起,她的父母就常把她送到外祖母这边生活并上学,隔上一段时间又把她接回去,转上省城的学校,末了总还得再送回来。俞怀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跟她不一样,他们也常到外祖母家里做客,却从来不需要像她一样寄寓于此并不断地把学籍转走再转回来。
那时候母亲对让她奔波的解释是家里的住房困难,在那些年月里他们家只有一间房子,是俞怀颖父亲单位分的,这一间房子要挤下五口人的确困难。俞怀颖记得当时他们家就一张大床,父母和弟妹挤在一张床上睡,她则睡在一张木制可折叠的沙发上。但是俞怀颖外祖母家住的也不宽松,这边只有两间老屋子,一间住着俞怀颖舅舅一家,外祖母住另一间,外祖母那房间小得只能放一张床,俞怀颖在外祖母家只能跟外祖母一起睡,那房间里连张桌子都放不下,俞怀颖每晚上都得四处找地方做作业。在她的印象里住房问题肯定不是母亲把她送到外祖母这里的主要原因。
俞怀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母亲,俞怀颖所有的亲人里只有母亲真正疼她。她一直记着当年母亲牵着她的小手,坐着汽车从省城来到外祖母家时的情景,那些天里没有哪一天母亲不暗自垂泪。当母亲离去她跑到门边喊“妈妈”时,她总能感觉到母亲难以割舍痛不欲生的心境。从很小的时候起俞怀颖就断定让她不得不往外祖母家去的是她的父亲,俞怀颖管他叫“爸爸”,在心里她一直对这个父亲表示怀疑。俞怀颖的父亲在政府机关里工作,一向忙忙碌碌,不太管家里的事,他对俞怀颖不见得不好,他在发怒的时候会打人,俞怀颖的弟弟妹妹都挨过他的痛打,他却从来不打她,只是横竖看她总不顺眼。他嫌俞怀颖吃饭时声音大就跟猪吃食一样,无论俞怀颖多么小心多么注意他总要嫌弃,俞怀颖非常不平,她觉得她的弟弟和妹妹吃饭声音更大,可父亲从来不说他们。俞怀颖的父亲还嫌俞怀颖成天阴着脸没有一点笑容,他说:“我们家怎么就出个哭丧鬼,你整天脑子里都转着些啥?”他也讨厌俞怀颖读书做作业的姿势,他说你总在书上啄什么你是只鸡吗?每当父亲嫌她的时候母亲就急忙出来把女儿拉到一边,摸着她的脸说:“爸爸是为你好。”那时母亲的眼眶里常会泪水盈盈,就是这些泪水让俞怀颖把心里的所有不平都吞忍下去。俞怀颖从小非常懂事,绝不愿伤害自己的母亲,也不想让父亲不高兴,可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没法获得父亲的喜欢。父亲有无数理由对她表示不满,有一回她在无意中听到父亲向母亲发火,父亲问母亲是不是把好东西都让怀颖吃了,否则为什么光见她长高,两个弟妹都那么又瘦又矮?
因此俞怀颖怀疑“爸爸”不是自己的真正父亲。她注意观察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她感到他们都很像“爸爸”,他们都是矮个儿,她却长得苗条高挑,她跟他们真不像同一个父亲的孩子。
俞怀颖记得有一回母亲把她送到外祖母家时,外祖母曾冲着母亲唠叨说:“又来了,看看你弄成啥样?早不听我的,现在还怎么?送她找老爹去,送去?”
母亲被外祖母说得眼泪汪汪。那时俞怀颖还小,她们以为她还不懂事,实际上她把什么都听在心里。
她想:“难道我还另有一个老爹?”
俞怀颖的外祖母是个喜欢唠叨的老人,她收留养育俞怀颖,对自己的外孙女不坏,但是脾气不好,特别会数落唠叨。老人家日子过得很不舒心,她早年守寡,独自拉扯起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俞怀颖的母亲是老大,嫁到省城去了,俞怀颖的舅舅生得很清楚,却因早年患流行性乙型脑炎留下后遗症,成个傻子。俞怀颖的外祖母守着这个傻儿子,把他养大,给他找了个哑巴姑娘结婚,然后照料他们生的儿女,日子过得格外艰辛。在俞怀颖的记忆里老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唠叨抱怨,在这个家庭里除了俞怀颖没有谁可以充当老人抱怨的对象,于是俞怀颖便时时淹没在老人的唾沫之中。老人对俞怀颖抱怨自己命苦,抱怨哑巴儿媳迟钝,抱怨当初给傻瓜儿子治病的那个医生害死人,老人说看这情形当初那医生还不如把人治死算了,省得她一辈子当牛作马。老人也抱怨俞怀颖的母亲,她说这个女儿当初太不懂事,太不听话,要是听她的话,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俞怀颖似懂非懂,老被外祖母说得一头雾水,在她的感觉里母亲一向非常懦弱,她怎么可能是个不听话的姑娘,怎么可能违拗外祖母的意愿,做出些让她至今喋喋不休的事情来?俞怀颖在外祖母这里从来都得小心,要是意外地做了什么让老人不高兴的事,她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从几十年前的事说起,直到眼前,她会抱怨俞怀颖跟她母亲一样总是惹她生气。顺便她还要痛骂俞怀颖的父亲,她说你那个该死的短命的老爹你叫他来看看!
俞怀颖总是恍然觉得外祖母的话里有话。
俞怀颖从小颠簸在父母和外祖母两个家里。两个家没有一个让她感觉到是自己的家,她一直觉得自己是粒皮球,在两个城市两个拥挤的房屋间被踢来踢去。她在哪里都像个多余的孩子,她意识到自己在省城那个家里比弟弟妹妹不如,在外祖母这个家里比她的傻子舅舅哑巴舅母也不如,不管怎么说她是寄人篱下。她似乎从一出世就是个劣等人,除了母亲,没有人给她足够的亲情和温情。小时候俞怀颖常独自一人看着天空做白日梦,她心里充满着跟她的年纪极不相称的迷茫,她怀疑自己的来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她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她非得永久地迷惘,永久地陷在遗弃和抱怨里?她总觉得自己是个迷路走失的人。所有这些迷惘她都只能深深埋在心里无从倾诉,她从小学会自己忍受遇到的一切,不管碰上什么委屈,她都不可能去向她的母亲,她的外祖母,或者舅舅舅母弟弟妹妹哭诉,没人跟她沟通,她只能把心锁起来,沉浸于自己的遐想世界。
母亲去世后,俞怀颖即向父亲提出回外祖母家去。她父亲因意外丧偶心情极度不好,一听俞怀颖的要求便暴跳如雷,他向俞怀颖大叫,说自己把她养育成人,从来没有亏待她,为什么她总跟他格格不入,根本不像他的女儿?父亲说:“你要再不把这里当做家你就永远别给我回来。”
那时俞怀颖已经长大了,她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愿,她表面平和,沉默寡言,却坚韧不拔,绝不屈从于别人,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办。她对父亲说:“妈已经死了。我永远不会再回这个家了。”
她离开省城,投奔外祖母。外祖母见到她时垂首而泣,说:“苦命啊,苦命啊。”
她跟着外祖母生活了几年,高中毕业后以高分考入大学,在填报专业时她尽弃大家热衷的商务法律新闻一类热门去向,选择了考古一行,学校的同学和老师均大惑不解。她说:“我就想干这个。”
没有人知道她有一个身心大惑。她在淡漠的外表下时常沉迷于根的思索,像她这样的人通常有一些奇怪的念头,且异常执着。
俞怀颖曾向外祖母谈及她的迷惑。外祖母挥手顿足大叫道:“小孩子家都想的啥!你爸爸对你不坏了,每个月寄钱供你上学,没了他你去扫大街呀?”
俞怀颖的外祖母在她读大学三年级时去世,享年七十有余。老人命途多舛,末了还算善终。俞怀颖得知外祖母死讯,从学校赶回家乡时,老人已经入土,傻子舅舅和哑巴舅母什么都不懂得说,俞怀颖觉得最后一扇门在自己眼前闭合,随着外祖母的去世,某些有关她的往事便永久地成为谜团。
于是她日渐沉默,她在毕业回到家乡后沉迷于她的工作,表面平和,却总拒人于千里之外。时日渐深,开始有人在她身后指指点点,谈论她的奇特和孤单,她想她差不多已经陷入了某种异于常人的境地。
有时她独自极目远眺,恍惚间她总觉得会有一个神秘的人自天而降,凑在她的耳畔耳语般跟她说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