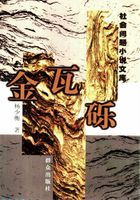
第4章
齐惠的母亲为齐惠准备了一提包东西,提包未上锁,周四平一回家就把提包拉链拉开,检查里边的东西。他发现里边就是些衣物,外加一个封了口的沉甸甸的信封,周四平出于好奇,用一根大头针把信封口弄开,发现里边整整装了两千多块钱。
周四平对自己说:“这家人真他妈的。”
周四平坐火车风尘仆仆回到学校,第二天就拎着那提包去找齐惠。齐惠住女生宿舍楼,她那宿舍住八个女生,因为寒假还没完,学生都还没回来,齐惠是自己一个呆在宿舍里。周四平敲门时听到里边有一个声音,他很吃惊,他觉得那很像是个哭声。打门后那声响没了,隔会门开,周四平看到齐惠站在门边,一脸的怒容。
“你家寄东西了。”
“不要。”
“不要归我了。”
周四平扭头就走。
隔天齐惠到男生宿舍找他来了。齐惠说:“我爸打我电话了。东西给我吧。”
她说昨天她是心情不好。她碰上了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她发现自己给人耍了,耍她的竟是自己最在乎的人。她不回家过寒假,她从东北匆匆赶回学校全为了这个人,谁料到这竟是个胆敢欺骗和玩弄她感情的最坏的混蛋。
周四平问:“要我帮你不?”
齐惠说:“听说你这人特实际,你帮我的忙给自己图什么?”
周四平说:“我当然得图点东西,那对你来说不难办。”
“要钱?”
“不。”
于是齐惠请周四平当晚去校园外的一家酒店,那是这一带最豪华的一家酒店。他们在酒店的咖啡厅一张桌子边等了一小会儿,有位大高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走了进来。
齐惠说:“就是他。”
周四平走上前去,突然一抬手,用力打了小伙子一个耳光。
“你小子比我结实,你也可以给我一下。”周四平说,“咱们试试?”
小伙子捂着脸颊,两个眼睛往外喷火。他说:“你是谁?”
“我,周四平。经济系的,四年级,你打听去。”
小伙子捂着脸转身走开。
那时周四平才发觉自己浑身都汗湿了。他知道对方经常练哑铃喜爱拳击并踢足球,对方要真给他一下他肯定要鼻青脸肿倒地不起接近呜呼哀哉。
半年后周四平从学校毕业,分配回到家乡,进了市工商银行。那是个热门单位,谁也想不到周四平那么有本事能把自己就这么弄进去。有人问周四平怎么会攀上工商银行的副行长齐长安并因此进了银行,周四平自我解嘲道:“我这种人还能靠什么?老天爷一不留神给了我一个机遇。横下心,敢冒被打个半死的危险,这就行了。”
倒是齐惠自己毕业分配出了些麻烦。齐惠的父母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小女儿,他们有能力为女儿在家乡找一个好单位,偏偏齐惠不感兴趣,她想去大地方,去北京,她瞒着父母跟北京一个中直部门联系,基本谈成。分配前夕,她父亲齐长安得知情况,跑学校上北京下省城,想尽办法把女儿弄回去。齐长安说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不操心儿子但是他对这个女儿绝对放心不下,女儿要真去了北京,他和孩子的母亲只好辞了职跟着去了。齐惠拗不过父母,怏怏不乐回到家乡,她赌气不去父亲给她找的热门好单位,一口咬定要去广播电台当节目主持人,这一行当跟她的外语专业根本对不上口,可她就是要去。齐惠在大学里当过校广播站的学生节目主持人,她择业的灵感可能来自那段经历。
一年后金子也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回本城一所中学教书。她跑到周四平在工商行的单身职工宿舍做客,她说:“阿平你到底离开了咱们的破巷子。”
金子笑道:“阿平,有一天有人会用刀子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个什么鬼样。”
周四平知道金子的笑语后边藏着些什么。他能感到自己的心也在隐隐作痛,但是他在这一问题上一向非常冷静。他知道自己可以向金子伸出手去,他们可以省吃俭用,每个月从各自微薄的工资里抠出一点来存进银行,他们还可以到处借贷,凑上几万块钱参加集资建房,费尽千辛万苦弄到一套位于顶层或者最下层的小小套房,然后装修房间,购置家具,办几桌酒席,在酒席上一边劝酒一边暗自心痛酒钱,盘算着日后如何还债,婚事未过就瘦得像一只公猴和一只母猴,躺在床上互相抚摸时都像在弹奏琵琶。然后生儿育女,政策允许的话他们可以生出一堆瘦巴巴的猴子,他们将在一个日渐陈旧乱蓬蓬局促肮脏有如猴窝的寓所里度过此生。
周四平为自己描绘出如此清晰的图景以自醒,他知道自己得另辟蹊径,他有一个可能,他没有权利不去试试。
他频繁出入于齐长安的家中。齐长安是他的行长,他跟齐长安有许多可以触及的话题。周四平分配到市工商行后工作尽心尽力,又勤快又有头脑,颇得齐长安欣赏,他出入齐宅或汇报事务,或提工作建议,也帮助处理齐家杂事琐事,手勤脚快,极得人心。那个时候齐长安夫妻正为宝贝女儿齐惠大伤脑筋,因为齐惠对父母一直耿耿于怀,这女孩非常任性,她用各种花样气恼自己的爹娘,让他们饱尝干涉她自由的苦果。齐惠一天到晚在外边玩,身边跟着一群得天独厚无所顾忌的青年男女,其中大多很有背景出自本城某个名门。这些人在一块疯了似的吃喝玩乐,追星飙车,跳舞打牌无所不为,据说他们混在一起还偷看黄色录像,一些行径接近于性乱,要不是都很有来头可能早被警察一锅端了。齐长安夫妻忧心如焚。
周四平成了齐长安抓住的一根稻草。齐长安说:“你们是同学,你要帮帮她。”
周四平盯住齐惠,俨然以奉命充当保护人的身份自居。他打电话到市广播电台核实齐惠的行踪,到处打听她的活动情况,并几次深入一些极其可疑的场所,以其父母的名义,把醉得几乎不省人事的齐惠拖回去交给她的父母。
齐惠说:“你真是一条狗。”
周四平道:“你和你那些纨绔子弟比不上我,猪狗不如。”
后来有一天齐惠忽然打电话把周四平约到一家酒楼,说有要事跟他商量。周四平去了,两人在一起吃饭,齐惠于席间提起大四时让周四平跟她到咖啡厅去打人那件事,她说:“现在又用得上你了。”
她出事了。她跟一些男孩玩得过分且未注意防范,怀孕了,她得赶紧上医院做善后处理。这事瞒不过她的父母,因为某种原因她没法让肇事者出来承担责任,她得找一个无关者来对此负责。
周四平冷笑道:“你认为我一定会答应你?”
齐惠说:“你肯定认为这是个机会。你当然可以提出一些条件。”
她说她已经觉得挺累,她对自己的父母似乎过分了些,不管怎么说父母一直是对她非常好的,不应当让他们承受他们实在受不了的打击。她觉得似乎再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她想这回大约得试试其他的解决方式。她问周四平是不是读过一本书,这本书是十八世纪法国一个叫做司汤达的名作家写的,书名叫做《红与黑》,书中有一个人叫做“于连”。她说,“你就是那个于连。”
周四平装傻。他说他没读过这书。他说:“怎么法国人也姓于?”
半年后他们结婚。在婚礼上周四平精神抖擞,齐惠气质绝佳,一出婚姻戏演得相当到位。那时齐长安已经升任市工商银行行长,手握本地金融重权,影响重大,单位特意给行长的乘龙快婿周四平分了一套新房,承蒙岳父岳母关心,周四平的新居装修得非常够水平,在外人眼中有如宫殿,连周四平自己走进家门都不免头昏目眩,恍如进入梦幻世界。作为一个性别倒置的当代“灰姑娘”,周四平颇有一步登天之感。
周四平和齐惠结婚前,齐长安跟周四平长谈了一个晚上。齐长安说:“齐惠是被我们惯坏的。她任性,随心所欲,还有很多毛病。你要容忍她,不管怎么样她都是我和我妻子的命根子。”
周四平说:“我知道。”
后来周四平一帆风顺,几年中从一般办事员升到科长,然后进入企业界,接管经委属下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靠着自己的眼光和胆识,凭借着强大的金融支持,周四平创造奇迹,脱颖而出。人们用一种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很少有人知道他生活中永恒的暗淡。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周四平跟齐惠就住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们从不吵架闹事,只是各管各的形同路人。齐惠在婚后忽然变了一个样子,不再像原先那样玩世不恭,倒不是她觉得有必要对这个婚姻承担什么责任,她只是对往昔的任性行径感到厌倦。她忽然想试一试自己在主持人行当里能够有多少发展余地,她便稍微投入了一点,不料仅仅那么一点就让她冒了出来,成了一个众人瞩目的主持人。齐惠不愧出自名门,有一些来自久远的东西简直就是埋藏在血液里的,这些有时被称为“气质”的东西一旦表露便光华四射,世人只能高山仰止,自叹弗如。齐惠不管是早先迷失还是此后回归从来都旁若无人,她从不跟周四平说什么,她看着周四平的眼光永远像刀一样锋利,没有谁能像她那样把他看进骨髓。这种眼光让周四平恨之入骨,他有一种冲动,发狠有朝一日要把这种眼光彻底踩在脚下。但是无论周四平如何努力,无论他如何日益引人注目,齐惠看着他的眼光始终没有任何的变化,她使周四平无时无刻摆脱不了一种深刻得无可形容的沮丧和失败感,尽管他表面上笑语不断,轻松自如。
分手时金子掉下眼泪。
“到头来可能都一样。”她摇着头哽咽道,“一无所获。有一天会忽然发现追求的一切是空的,得到的一切也是空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那么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周四平离开时,金子跑进屋里,她说:“等等。”
她从屋里取出一把伞,撑开来遮在周四平的头上。周四平看到她泪眼迷蒙。
那时有细雨从天上飘落下来。
俞怀颖用一把剪刀剪开信封,抽出一张薄薄的信纸,她注意到那是一张小学生的作业纸,有人在上边写了几行钢笔字,字写得棒极了有如硬笔书法展览上的作品。
信发自城郊三塘村,寄信人自称“一民众”,信中反映三塘村近日因修路挖到一座古墓,墓中发掘出的一些物品现流散在村民手中。这古墓看起来年代久远,里边的东西很可能是些珍贵文物,写信者认为他有必要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
俞怀颖把信收了起来。她看看表,略略收拾一下办公桌上的东西,起身出门。她跑到办公楼外自行车棚那里,推出自行车奔三塘而去。
俞怀颖去过一次三塘,那个村子就在市郊,自行车半小时可到。上一次她到三塘也是因为一件文物方面的事情,当时她听说三塘村外的一个工地挖出了一个古算盘,专程跑去看看。此后她一直很注意那个村子,她认为那个村子可能座落于某一个晋代废墟之上,总觉得那里也许真会发现一些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