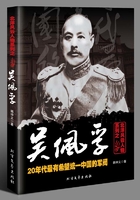
第5章 直皖战争
高碑店,一所小学校里。
街口放着岗哨,门口站着卫兵,院内拴着鞍韂齐备的马匹。一根根电话线从四面八方引来,集中在一排教室里。嗒嗒的无线电讯号,奏出紧张的乐音。这是京汉路上的一个小站,距北京约八十公里,距敌前沿阵地只有十来公里。
大教室里,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身着戎装,神气活现,在作大战前的动员。眼前列坐的是他的旅、团级长官。他说:“就我本意讲,我不愿打仗,是段祺瑞逼的,我无法选择。毋庸讳言,仗打好了,我们风光无限;仗打糟了,我们一块完蛋!我先说说战局……”
7月8日,段祺瑞在团城组成定国军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任参谋长兼东路总指挥,段芝贵任西路军总指挥兼京师戒严总司令,下辖曲同丰的第1师、刘询第15师、陈文运第3师,还有两个骑兵团,一个重炮营。曲同丰担任主攻,刘询担任侧攻,陈文运作总预备队。西路为主战场,攻击目标直指保定。东路为辅战场,参战部队有马良第2师,魏宗瀚第9师,宋子扬、李如璋两个旅。攻击目标直指天津。东西战场都有日本顾问助战,皖军投入兵力六七万人,有飞机大炮作战术配合。前不久,段祺瑞借日债八百万,为士兵发了足饷。
7月9日,直军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曹锟自任总司令,大本营设在天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东路有曹锳的第2师,李殿荣的第2混成旅,省直及天津市守备队。西路有吴佩孚的第3师,王承斌、萧耀南、龚汉治、彭寿莘四个混成旅。共计四五万人。从人数、装备上讲,皖军明显占优势。
与此同时,奉军第27、28师各一个旅调到天津地区,总司令是张景惠。
吴佩孚扫了大家一眼,说:“弟兄们,从人数、装备上讲我们占劣势,但吴某打仗一向出奇兵、用奇谋,以少胜多。哈哈,对打赢这一仗我是有信心的!以前我们发过‘讨逆令’,没有涉及段祺瑞,事已至此,我不再客气。参谋长把元电念给大家听!”
李济臣起而念道:“……自古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钧,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外债以残害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军队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我民之血,绝非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功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尚闻大义,誓不与张邦昌、石敬瑭、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而后亡。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今日之战,为救国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
吴佩孚首次点段祺瑞的名,首次指责他“卖国”,称他为“汉奸”、“国贼”,发誓与他“不共戴天”。
此电一出,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赵倜等相继发出“讨逆电”,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对安福系、徐树铮大张挞伐,历数段祺瑞三大罪状……由此,段祺瑞“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话被打破了。同时,奉军侦破一起以姚步瀛为首的十三名奸细案。经审讯供认,他们系皖系干将曾毓隽所派,并有定国军委任状和十二万元活动经费;并供认此事已商承段祺瑞和徐树铮,其使命是刺杀张作霖,发动政变……这样一来,段祺瑞彻底把张作霖推向直隶一边。张作霖发誓:“与直军共举义旗,讨伐诸奸!”
讲话完毕,吴佩孚把郑博言叫到密室,小声地说:“小郑啊,听说你在刘询手下当过参谋,跟旅长张国溶相交甚厚,我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他揽着郑博言的肩,“你化装去刘询的兵营,劝说刘、张不要替段祺瑞卖命。你说,你们都是冯大总统的旧部,受过段祺瑞、小徐多少窝囊气?冯大总统下台后,他们更拿你们不当人。你多提你舅父张联棻,他们跟你舅父有深交。”
郑博言说:“放心吧玉帅,这事包在卑职身上。刘、张旅长跟我如同家人,另一位旅长齐宝善和我关系也不错。我曾几次劝他们投效玉帅,他们说苦无机会,他们早就受够小徐和段芝贵的窝囊气了!”
吴佩孚一拍郑博言的肩说:“好小子,事成之后我提拔你当总部参议,中校军衔。我有一封亲笔信交给刘询,他知道怎么做。”
郑博言把信藏好,给吴佩孚敬礼而去。
1920年7月10日,直皖战争在琉璃河打响。
枪炮声响彻夜空,把黑夜照如白昼。定国军一师的骑步兵,猛攻直军阵地。直军毫不示弱,拼命抵抗。皖军一次次被打退,阵地前留下一具具尸体。皖军后继部队冲上来,夺占直军阵地,直军来了个反冲锋,又把阵地夺回来。战斗持续到次日拂晓。
“丁零……”电话铃响。主阵地营长拿起电话:“喂,长官,阵地让我夺过来了,很牢靠……什么,撤?为什么要撤?我能顶住!什么?玉帅的指示?是,是,马上撤!”
黎明,皖军又发起一次大规模冲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占领阵地。但见阵地上丢盔弃弹,十分狼狈,到处是仓皇逃窜的痕迹。皖军立刻向曲同丰报喜。
皖军被胜利鼓舞,乘胜追击。
王团长的先锋连立功心切,快速出击,只见直军如狼奔豕突,四散惊逃。剩下的大炮、弹药车孤零零留在路上。皖军围上去,想把大炮、弹药箱拖走。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轰隆隆”几声巨响,一百多人的残肢断臂随着断木碎铁飞上天空。原来废炮里、弹药箱里全是烈性炸药。直军的逃跑、丢枪弃弹是吴佩孚的诱敌之计……
王团长不顾伤亡,命令部队向前推进二十多里,把吴佩孚的前沿指挥部——高碑店团团围住。
曲同丰急忙向总指挥段芝贵报功。段芝贵一手搂着名妓筱翠云,一手拿电话:“好,好,我给你记头功,其他人一律论功行赏!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敌指挥部拿下来,活捉吴佩孚!”
本来,曲同丰应与刘询协同作战,他怕刘询夺头功,所以,只顾自己前进,不问刘询是否跟上。他投入最大兵力,把前沿指挥部安在离高碑店只有十几公里的松林店,命令部队向高碑店发起总攻。当皖军到达距高碑店只有三四里地的一块洼地时,突然,从两侧树林、高地和庄稼地里射来狂风骤雨般的子弹、炮弹,几千皖军被困在垓心。直军凭着人多势众,借助地形优势,很快把皖军消灭殆尽。
曲同丰十分恼火,决定孤注一掷,投入两团兵力,向高碑店猛冲……
令他茫然的是,当部队冲到高碑店外,除踩响大片地雷外,没遇到任何抵抗,轻轻松松进了高碑店,占领了吴军司令部。曲同丰气得大骂:“娘的,这是打的什么仗?!”
不管怎么说,不到两天,推进一百二十里,虽伤亡千余人,但毕竟占领了高碑店、松林店、涿州几个重镇。为此,皖系各报纷纷派出记者赴前线采访,天津、北京及日本人的报纸,连篇累牍,大肆渲染皖军胜利。
就在段芝贵、段祺瑞做着黄粱美梦时,郑博言回到吴佩孚身边。郑博言按捺不住惊喜地说:“玉帅,成功了,成功了!我见到刘、张、齐三人,他们决定响应玉帅号召,不再为段祺瑞卖命,这是他们的共同声明……”
说着,把一份声明稿拿出来递给吴佩孚。声明包括四项内容:一、本派官兵绝不互相残杀,从即日起退出战斗;二、清除段派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人;三、取消蒙古筹边使,解散安福系;四、拥护大总统……
吴佩孚高兴地说:“太好了!这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要大反攻了!郑博言,你立了大功。刘询还说什么?”
郑博言说:“他说他的军队处在皖军包围之中,还得做做样子,打打空炮,请直军别误会。他还说,他要在适当时候,把这个声明通电全国。”郑博言把嘴凑到吴佩孚的耳根小声说,“张、齐二旅长也要投到这边来,让我跟你商洽具体时间和办法。”
吴佩孚一拍大腿说:“太好了!刘询呢?”
郑博言说:“他态度暧昧,对老段仍抱幻想。”
郑博言走后,李济臣慌里慌张走来:“东线来电,情况不妙。7月14日夜间,东线战斗与西线同时打响。皖军从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阵地猛攻,直军在铁路桥上架大炮阻击。双方对峙一天不分胜负。不料,16日早晨,驻天津日军护路队,借口铁路是非军事区,强迫直军退出铁路两英里。这样,我军防线打开缺口,皖军乘虚而入……”
吴佩孚骂道:“他妈的,这是小日本儿的阴谋!”
李济臣说:“是的,可是没办法。直军被迫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三天打了两仗,都是我军败北,曹锳、曹锐向老帅求援。老帅给张作霖发电,请他派兵救援,还说请他派兵援保。张作相的27师,吴俊升的28师,孙烈臣的29师已经入关,明日可到达战场。”
吴佩孚说:“唉,糊涂!怕是请鬼容易送鬼难呐!你告诉萧耀南,一、多派小股部队扰敌,不给他喘息之机;二、多埋地雷,封锁桥面路口;三、命部队饱吃足喝,休息待命,准备大反攻。我要给段芝贵一点颜色看!”
17日下午,吴佩孚命部队杀猪宰羊,饱餐一顿;又命后勤处发给战士每人五块大洋,长官十块。吴佩孚到各团营去看望官兵,给他们训话、敬酒。官兵们群情激扬,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时,天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红土地十分泥泞。吴佩孚在马上仰天大笑:“哈哈,天助我也!”因为一下雨,皖军的重武器推不走,拖不动,再也不起作用了。
晚8时30分,战斗打响了。直军吃饱喝足,口袋里装着光洋,左臂扎着毛巾,向松林店、下坡店发起冲锋。皖军难挡直军攻势,纷纷把难以拖走的大炮、重机枪、辎重弃于路旁,直军炮口一转,用皖军武器轰击皖军,很快把松林店、高碑店夺回来,曲同丰率部狼狈跑进涿州。
曲同丰龟缩弹丸之地,不时给段芝贵发急电,请求派刘询、陈文运前来支援。段芝贵有苦难言:刘询的两个旅已投降直军,刘询率部撤出战斗;陈文运被困在七八十里之外动弹不得。
曲同丰等不来援军,急得团团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部下喊:“吴将军特使到!”
曲同丰迟疑地说:“特使?请!”
不一会儿,吴佩孚的特使张佐民走进来,给曲同丰行了个军礼:“吴将军命我送来一封信,请将军览阅。”
曲同丰哆哆嗦嗦展开信,上写:“老师(曲同丰在武备学堂曾是吴佩孚的老师)素日讲学,常云军人以卫国为主旨。吾与师兵戎相见,宁不知罪?为国家元气,两相罢兵,安敢与师相厄?请师赴我处议和,旦夕可定也……”
曲同丰想,自己被围,处境甚危。刘、陈二师远水难救近火,自己与吴佩孚有师生、同乡之谊,料无意外,不如跟他周旋,拖延时日,等待援兵,再作计较。
曲同丰带了几个随从,随同张佐民来到吴军司令部。吴佩孚向曲同丰行个军礼,笑嘻嘻地说:“老师,多年不见,你一向可好?”
曲同丰说:“托福托福。子玉,你把我叫来有何见教?”
吴佩孚说:“很简单,请发布停战令,对你我都有好处。”
“我还有援兵。”
“可惜远水难解近渴。”
“我还有刘、陈两部可为支援。”
“你看这个……”
吴佩孚拿出刘、张、齐的那份声明书。曲同丰一看泄了气,但还在嘴硬:“我东线打得很好,还有胜算。”
吴佩孚拿出一份电报稿说:“你再看这个……”
曲同丰接过一看,东路皖军已在奉军夹击下溃不成军,徐树铮等逃进北京六国饭店……曲同丰惊出一身冷汗,他还想谈条件,吴佩孚说:“败军之将,无权谈条件。”
曲同丰叹口气,说:“我投降……”
直军顺利占领涿州,不失时机地沿铁路向北追击。陈文运哪里还敢抵抗,如丧家之犬,退回北京藏匿。段芝贵见大势已去,先于陈文运带着几个妓女逃回京城。
7月18日,曲同丰偕多名将领,在保定“光园”向曹锟举行“献刀”仪式。曲同丰满脸苦笑,双手把象征权力的军刀献给曹锟:“誓不再与贵军为敌。”说罢,两行浊泪汩汩而下。曹锟笑道:“哈哈,本使愿接受贵军投降,当以优待俘虏之条例,善待诸将,不予追究个人责任。”
曲同丰等感激涕零,当天领衔发出通电,劝定国军与直军共同讨贼。
直皖战争前后只用七天,就以皖系失败而告终。
段祺瑞像关在笼子里的恶狼,张牙舞爪,狂躁不安。他把窗子全推开,把上衣纽扣全扯开,呼呼地喘粗气,两行浊泪从憔悴的脸上淌下来。
“咣当”,门被撞开,段芝贵像一团肉球滚进来,声嘶力竭地喊:“芝帅,完啦,全完啦,我们失败啦!芝帅,你杀了我吧,省得留在世上丢人现眼!”
段祺瑞慢慢坐下,有气无力地说:“怪我,我无颜见江东父老。算了,算了,人生如梦,该收场了。”段祺瑞扬着头泪流满面。段芝贵匍匐向前,抱住段祺瑞的大腿,说:“芝帅,你别太自责了,都怨部下无能啊!我、我不能久留,他们会来抓我的。对不起,我、我走了。”说着,身子像安了弹簧,跳起来跑了。段祺瑞把一只茶杯掷出去:“滚,都给我滚!”
段祺瑞独坐沙发上,紧闭双目,像一具僵尸。但他的脑子并没有闲着。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在盘点自己的家底,如何东山再起。
直皖战争初起时,他曾电令吴光新、张敬尧到河南进袭直军后方,命安武军李承业部进袭河南东部,命驻洛阳的边防军进袭郑州,命山东马良由济南进袭德州的商德全。但吴光新、张敬尧受王占元、陈光远的牵制,安武军受张文元直军的牵制未敢行动。当时,段祺瑞骂他们胆小怕事。但现在看来,他们没有动作倒对了,皖系的力量得以保存。只有马良听话,把所部从济南开到德州与商德全对阵,结果马良因战争罪被迫解职,所部被田中玉收编。驻洛阳的边防军宋邦瀚、张鼎勋二旅,因拒绝吴佩孚收编而哗变,驻库伦的褚其祥因远在边陲而获保全……
此外,各省的皖系军阀为数不少。如山东田中玉,安徽倪嗣冲,浙江卢永祥,福建李厚基,山西阎锡山,陕西陈树藩、刘镇华,甘肃张广建都未受到任何损失。自己有这么大势力,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佩孚吗?这么一想,段祺瑞心里安定许多。
“报告!”段祺瑞的副官进来说,“咱们的溃兵退到城下,可城门紧闭不开,他们又闹又骂,说不开门就轰城,谁也别想活。”
段祺瑞霍地站起来:“备车!”
段祺瑞驱车来到总统府,不似以往那样居高临下,一见徐世昌,他老着脸皮说:“大总统啊,看在兄弟情分上,放他们进来吧。”
徐世昌拉着脸说:“进来?北京治安怎么维持?你我安全谁来保证?”
段祺瑞也急了:“不进来怎么办?激起兵变我们一起完蛋!”
徐世昌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先你要听我的话,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唉,什么话也别说,我不愿打仗,是吴佩孚逼的。好老兄,你就帮兄弟一把,补一道‘停战令’吧。”
“吴佩孚他肯听我的?”
“试一试嘛。”
“好,我发。你也得发一个‘引咎辞职’的通电。”
“我发,一定发。”
连日来,段祺瑞如丧考妣,曹锟、吴佩孚却是扬眉吐气。天津、保定等直系城镇张灯结彩,大庆三日。曹锟大戏院从京津两地请来杨小楼、荀慧生、梅兰芳、金达子等戏剧名优,唱大戏七天,戏院场场爆满。曹锟巧立名目,一声令下,各行各业,各村各镇,户户捐款作庆祝费。号令一出,白花花的银子流入新贵的腰包。
八月上旬的一天,曹锟大戏院召开庆功授勋大会,由总统特使向几百名各级功勋人员宣读任命书。这些任命是经过直奉两系讨价还价而成的:
一、撤销曹锟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改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三省巡阅副使,孚威上将军;二、升任李纯为苏、皖、赣三省巡阅使,齐燮元为副使;三、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四、王廷桢调任祯威将军,改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16师师长;五、直军各旅长一律晋升师长,提升王用甲、董国政、彭寿莘、孙岳为混成旅旅长;六、张作霖晋升镇威上将军,李纯晋升英威上将军;靳云鹏、王占元、赵倜、陈光远均授陆军上将,吴佩孚、王承斌授勋二位;七、曹锟由徐世昌“特令嘉奖,以彰功绩”。
细心人不难看出,这里独独漏掉一个张学颜,吴佩孚连旅长的位子也没给他留下。
会后,直奉两系在惩办祸首,军事分赃,解决国会、内阁、外交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吴佩孚主张幽禁段祺瑞,解散安福会,查抄祸首财产充作军费;张作霖和徐世昌则相反,主张把祸首名单压缩到最低。对段祺瑞不但不问罪,而且厚礼相加,各省皖系地盘不予更动,安福分子不予追究,对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亦然。曹锟怕把关系弄僵,最后来了个折中方案:把祸首限定在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十人。
张作霖之所以主张宽宥,是想拉拢这股势力为己所有。
在军事分赃上,两系几近动武。对战争的胜利,张作霖说:“你吴佩孚一个小小师长有多大脓水?老子光师长就有十几个!不是老子拔刀相助,你能打败皖军?”吴佩孚跳着脚说:“你张胡子算老几?不是我涿州一战打败曲同丰,皖系能失败?你张胡子还不是投机取巧,坐享其成?!”
战争没结束,张作霖就把大批辎重军资,装了一百多车皮拉回奉天。吴佩孚闻知暴跳如雷,急命萧耀南去炸列车,可惜为时已晚。不仅如此,张作霖还捷足先登,派兵抄没祸首财产达几千万……
在改编残兵败将上,争夺更加白热化。奉军抢先把小站龙济光部收为己有,又将西北军宋子扬部改编。直军也不示弱,将皖军第9、第15师改编,把刘询、魏宗瀚免职,让陆锦、齐宝善分任两军师长。对第1师、第3师两系争得不可开交,徐世昌出面调解才利益均沾。
在内阁问题上,徐世昌想让老友周树模组阁,曹锟想让老友王士珍组阁,张作霖则力主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
7月25日,长辛店的车站、大街打扫一新,从车站到吴军司令部岗哨林立,军警巡逻,昂首挺胸的军人唱着《登蓬莱阁》,列队走向练兵场。
大约九点多钟,十来名英、美等西方记者下了火车,他们在张其锽、李济臣的陪同下,走在田间小路上,感受“模范”军区的“民主和谐”气氛。他们见军人帮老乡田间劳作,挑水,扫街,公平买卖,纷纷把场面收入镜头。他们路过一个露天碾棚时,对眼前的事更感兴趣:只见一个四十多岁、文质彬彬的军人,穿一件粗布衬衫,一条旧军裤,打着赤脚穿一双旧布鞋,正帮大娘推碾子,他们有说有笑,不时逗得妇女们哈哈大笑。记者们纷纷照相,吓得妇女们惊慌失措。张其锽说:“玉帅,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当记者们得知他就是久负盛名的吴将军时,十分惊讶,“OK!OK”地叫个不停。吴佩孚与记者一一握手、寒暄。
记者招待会在小学校教室里进行,吴佩孚坐在学生桌前,回答记者提问。
问:阁下,依你之见,如何解决中国乱局?
答:敝人早于今年六月在武汉发表通电,必须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敝人仍坚持这一主张。
问:阁下能谈谈具体方案吗?
答:国民大会应采取“国民自决”的原则,由各县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推选代表,再由省级组织复选,如此由下而上,层层推选,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只有这样才具民主性。
问:阁下以为,召开国民大会以什么地点为好?
答:上海或天津,应躲开北京。
问;国民大会应解决哪些问题?
答:修改议员选举法,制定中华民国统一宪法,审查北京政府历年与外国所定条约、密约,审议中国所借外债及用途,抄没安福祸首不义之财……
问:关于总统问题,阁下有何看法?
答:本人一向拥护总统。但现在之总统系安福国会弁髦宪法之结果,是少数人操纵的,未得西南诸省同意,充其量为半个总统,必须由国民大会重选方能生效。
问:张作霖将军曾通电拥护总统,阁下意见岂不与他相左?
答:那是他的事,与我无关。
……
吴佩孚侃侃而谈,不时博得记者掌声。采访之后,他又与记者握手拥抱,合影留念,出尽风头。会后,他又领记者到兵营、练兵场参观,所到之处,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之后,他又与一个负有神秘使命的“记者”——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特使密谈一小时。最后,他用贴饼子、熬小鱼、山东煎饼卷大葱、小米绿豆饭招待他们。吃腻山珍海味的大鼻子们,对中国家常饭惊呼不已。
次日,《吴佩孚答记者问》、《吴佩孚印象记》、《直军军旅见闻录》和一张张大照片,连篇累牍发表在中外大报上,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媒体把吴佩孚吹得天花乱坠,吴佩孚再次成为风云人物。
吴佩孚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言论公开后,引起国人极大关注。不少阶层、团体、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谈话、文章,热烈响应。与此同时,也引起徐世昌、张作霖、曹锟、岑春煊、陆荣廷等各省大小军阀的惶恐不安。吴佩孚的主张发表后,正赶上张作霖、曹锟、靳云鹏召开天津会议,研究权力分配问题,他们一看报纸炸了锅。靳云鹏把报纸一摔,骂道:“什么他妈的国民大会,简直要咱们的命!”
张作霖气得浑身发抖:“扯谈!一个豆芥小官儿,也敢妄谈国是!”
杨宇霆说:“雨帅,不可轻觑这个豆芥小官儿,这小子手腕极高,极会哗众取宠,甚得民心,又有英美撑腰,得认真对付啊!”
张作霖说:“狗屁!他算老几?我只跟仲帅对话。理他有失身份!”
靳云鹏说:“宇霆兄所言不无道理,是不能小瞧他。我看这样,不妨见见仲帅,探探他的口风。”
张作霖坐车来到曹府。曹锟正在抽大烟,见张作霖进来,赶忙坐起来:“四弟,你也来两口儿?”
张作霖说:“不,我刚抽过。”
曹锟知道张作霖有事,立刻屏退左右。张作霖开门见山地说:“三哥,吴佩孚高谈阔论,胡说八道,你可知道?”
曹锟见张来头不小,搪塞道:“哈哈,子玉争强好胜,好出风头,四弟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头我说说他。”
张作霖说:“这种大事你宠着他,日后你怎么驾驭他?”
曹锟也正为吴佩孚信口雌黄恼火,但不敢难为他,更不敢得罪他,因为这点家业都是他挣的。他笑道:“四弟言重了,我与子玉是莫逆之交,他的脾气我了解。他说他的,我心里有底。看法嘛,每人都有,不一定件件能办成,只要我们掌握住定盘星,他能闹到哪儿去?”
张作霖顺坡下驴地说:“好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三哥,小弟告辞了。”